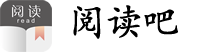明军无意攻击王欣诚的部队,这更让山西绿营的俘虏感到怒不可遏,不知道谁第一个跑到船边向着岸上的清军破口大骂起来,很快莫怀忠等在甲板上的军官也纷纷利用这个特权,用尽全力向王副将的军队喷吐着他们的愤怒。在这些军官的影响下,那些被关在甲板下的山西绿营士兵虽然上不到甲板上,也在船舱里跟着一起怒骂起来。
“断子绝孙的王欣诚!”
“兔崽子!”
“千刀万剐的王贼!”
上千人的谩骂声最后响得如同雷声一般,滚滚向岸边袭去。
甘陕绿营一开始还有些莫名其妙,但很快他们就听出了其中的山西口音,意识到擦身而过的明军舰队中大概装的是山西绿营的俘虏。
“是那帮山西佬么?”王欣诚的标营指挥在恩主身边,笑嘻嘻地问了一句。
“肯定的了。”王欣诚颇有点唾面自干的意思,虽受千夫所指,但却一点也没有生气:“肯定是那帮猪仔。”
“猪仔?”标营指挥有些疑惑地追问道。
“嗯,这是邓提督的原话。”
在和王欣诚达成协议后,心情愉快的邓名随口称王欣诚为卖猪仔的,但马上就意识到那都是华人的血泪史,在反省自己用词不当的同时,对这个字眼绝口不再提了。但王欣诚却听清楚了,牢牢地记住了这个词。一开始他觉得似乎用牛仔称呼这些被卖掉的山西佬更妥当,毕竟他们都是被折算成牛付给明军的,但细细一品味,王欣诚觉得这个词确实很妙。
“哈哈,确实是一群肥猪啊。”标营指挥哈哈大笑起来。
交易结束后,邓名按照惯例要付给王欣诚回扣,而王欣诚也意识到他一口气把辅兵都卖了会影响战兵的行军,就找邓名要了一些陕西民夫和几条船。现在王欣诚的士兵把辎重放在船上,不但行军步伐轻松,也完全不用提心吊胆,不用害怕会有明军的水师冲出来抢夺他们的盔甲。
完成交易后王欣诚也没有独占全部的好处,所有的军官和一百多个老兵每人都得到了一张释放证明。邓名保证见券放人,只要清军不曾杀害明军的俘虏(无论是不是属于邓名所部),那么这张释放券就不会被无视;理论上在战斗中给明军造成损失也不会导致释放券无效。但邓名有言在先,只有被俘者进入他的战俘营后这东西才有被认定的机会,如果因为激烈抵抗而导致愤怒的明军士兵拒绝持有人投降的话,邓名当然也不会追究他手下人的责任。
每个拿到释放券的清军士兵都小心地把它珍藏起来。有了这个东西后自己的性命也就有了保证,前提条件也都牢记在心,今后他们不会再杀明军的俘虏了,因为这基本等于自杀;上了战场就更好办了,反正打败了也不会丢掉性命,那还拼死抵抗干什么呢?
没有领到释放券的四百多个绿营新兵非常眼馋,不过他们还没有为王副将立下军功,交情显然也没到。不过军官们向这些新兵保证,只要他们以后在战场上勇敢作战,就可以得到释放券作为奖励——拿到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不必勇敢作战了。
“那些在船上骂人的,就是没有免死券的山西佬。”不少机灵的军官还趁机教育手下的士兵:“知道他们是什么下场么?他们都要被送去藏区,邓提督会用他们和食人生番换牦牛。那些番子有的是牦牛,就好吃个人肉。所以你们记住了,以后好好给王将军出力,不然就等着去喂生番吧。”
押送俘虏的明军舰队从重庆城旁边驶过,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后,俘虏运输船上的明军官兵都如临大敌,生怕被俘的军官又一次开始“集体跳江自杀”行动。因为所有的俘虏都是按人头和王欣诚折算了耕牛的,明军在把俘虏送上船以前也统计了数字,邓名并向押送的军官交代过:这些俘虏都是珍贵的劳动力,能够为成都政府创造财富,将来纳税后还会是兵源和税源,因此不允许虐待俘虏。如果在俘虏运输中出现了严重的减员,押送军官都要受到斥责,指挥官可能还会面临惩罚。
因此明军官兵对这些俘虏相当客气,见到有人落水时,第一时刻想到的是救人而不是放箭,甚至连不幸身亡者的尸体都被尽可能地打捞起来,以便向邓名证明这些人是“自杀”而不是被“虐待致死”的。
莫怀忠对这些政策自然一无所知,看着渐渐被抛在身后的山城重庆,他满心的悲凉和惆怅;而船舱中的士兵们得知已经驶过重庆时,也出现了低低的呜咽声。这些山西汉子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他们作为战兵,十个人里有九个会活活累死在军屯里,再也没有向孙思克和王欣诚讨还公道的机会,对命运的绝望让他们忍不住落下了男儿泪。
万县——重庆战役仍在继续,十数万明、清官兵仍在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不过对于这些越过重庆的俘虏来说,这场战斗和他们再没有丝毫的关系了。
又过了几天,在李国英仍尝试着突围、而邓名全力阻击的时候,明军的舰队抵达了叙州,并在这里把俘虏放下岸,交给袁象清点——押送官员自认为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俘虏下船时一个个红光满面。越过重庆后,押送的明军军官甚至允许士兵分批上甲板放风,以免他们在船舱里憋出毛病来。
出乎押送军官意料的是,叙州知府袁象亲自来岸边迎接这些俘虏,得知有上万名俘虏将被送来这里然后转运成都后,整个叙州都轰动了。
“兄弟们饿了吧。”袁象清点过人数后,笑容满面地把绿营的千总、把总都请到紧急搭建起来的大帐中,招待他们的食物很丰富,不但有新鲜的江鱼,蛋花汤,甚至每个军官还有一小壶新酿的酒:“快吃吧。”
莫怀忠怔怔地看着眼前碗里雪白的大米饭,这明显是刚刚收获的新稻,然后又掂了一掂分给他的一小壶酒,满满的,足有二两重。周围其他人也都在发愣。莫怀忠趁人不注意狠狠地抽了自己脸颊一巴掌,很痛,不是在做梦。莫怀忠周围的军官们也抽脸的抽脸,掐大腿的掐大腿,忙得不亦乐乎。明军的叙州知府亲自来迎接他们这些俘虏,提供的饮食更不用说,简直就是以往大捷归来的待遇——就是明军想招揽他们做炮灰,好像也没有必要这样吧?
袁象自从到了叙州后,一心想大展拳脚,把叙州建设得红红火火。不过就算刘晋戈是他过命的兄弟,也不可能在成都还急需劳动力的时候把大批的居民送来叙州——同秀才大部分也不愿意离开已经逐渐有了起色的成都,跑到叙州这个地方来,毕竟叙州的大部分物资还要仰仗成都供应。
袁象简单地计算了一下,要想让叙州的盐业和造船业大发展,他需要十万以上的工人,为了养活这些工人,他还需要至少这个数量的农民,为了满足农民和工人的需要,也为了让低税的农民心甘情愿地把余粮拿出来交易,袁象还需要大量的渔民、纺织工、铁匠、养殖户——这些人员成都现在自己都不够,不可能大量提供给叙州。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劳工荒让一心想大展宏图的袁知府愁得都生了好几根白发出来了——老袁家可没有少白头的传统,袁知府头上的几根白发真是太违反家族常理了。
这次邓名在叙州暂住的时候,袁象几乎每次会面都会提出搬迁人口的问题,但邓名也帮不了他多少忙。成都的人口眼下总共只有不到三十万,而刘晋戈一直在大叫成都府至少需要百万劳动力才能满足基本要求,就是五百万也不嫌多——现在刘知府恨不得邓名明天就去武昌把湖北搬空。
因此,刚一听说即将有上万俘虏过境后,袁象就下了决心要全力截留。这些绿营军官显然是俘虏中的骨干,袁知府抛下一切俗务跑来款待他们——因为没有人口,俗务也没有多少。
“肉馒头,随便吃!”在袁知府的大营外,叶天明带着手下的掌柜把铜锣敲得震天响,一屉一屉的馒头冒着热气,在俘虏面前摆成一座小山。和袁知府一样,叙州的盐商一个个也都觉察到了难得的机会,已经在岸边等候多时,俘虏们一下船他们就迎上去,想尽办法要让他们自愿留在叙州。
“叶老板,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几个彪形大汉冲进了盐商的队伍,为首的是个叙州船行的老板,带着伙计们来抢人。虽然他和叶天明一样都是刘曜的辅兵出身,但事关商行的生死存亡,川军的战友情谊也得向后放放了。
“来我们船行吧。”船老板说干就干,重重的一掌拍在一个山西人的肩膀上,沉重得就和他那根因为缺乏伙计而不得不摆在河边的新船的龙骨一般,这毫无预兆的一击差点把俘虏拍倒在地:“一天三顿饭管饱,学徒期也有二十元的月钱,学得快还有奖金!”
※※※
随着更多运输战俘的船只抵达叙州,本地的商行老板情绪也更加激动。第一批船运来了两千名山西战兵,然后是两千辅兵,第三波又是两千多山西人在叙州下船时,激动的叶天明等人看着眼前的精壮汉子,站在叙州码头上情不自禁地高呼:“提督万岁!胜利万岁!”
一万多山西人的到来,让叙州像是在过狂欢节一样。不过随着争夺劳工的战争如火如荼,狂欢气氛也变成了剑拔弩张。最后终于发生了暴力冲突,袁象在一天之内就听说了三起大规模的斗殴,小规模更是不计其数。
为了平息冲突,袁知府不得不派兵把老板们都请来知府衙门,旁听的还有正好来叙州公干的税务局长秦修采。不少人来的时候鼻青脸肿,还在衙门大堂上怒目相视。更糟糕的是,知府衙门并没有什么公正性,因为袁象不但是裁判,也是下场选手,他认为农业很重要,没有粮食就无法保证工商,在会谈上袁象祭出邓名的立方体理论,认为至少一半的俘虏都要去开垦土地。
顿时叙州知府衙门的大堂上就变成了斗鸡场,老板们和知府老爷吵成一锅粥。盐商声称盐业所需的人力必须得到保证,这是叙州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也是邓提督多次亲自过问的重点项目——懂得祭出邓名语录这个大法宝的人可不止袁象一个——而粮食完全可以去成都收购,要是刘晋戈不配合就从湖广运。盐商们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袁知府大力支援盐业,那粮食要多少有多少。
袁象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被盐商们一吵吵也没有了主心骨。见知府老爷居然有被盐商说服的苗头,船老板们急了,连忙奋起反驳:若是没有我们造船,就别想把盐运去湖广,更不用说邓提督已经有了最新指示,那就是不但要卖盐,而且还要卖船。至于从湖广运粮回来一事,船老板们更是痛加驳斥,指出这个根本就是赔本的买卖,别看盐商们现在答应得好好的,事后肯定反悔,袁知府切莫上当。
其它的木材商行、铁匠行也不甘寂寞,纷纷表示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船老板就算有伙计也造不出船。盐商也是一样,现在他们想节省人力用晒盐法,他们需要木盘,将来若是想恢复火井煎盐(天然气)也同样需要木材行和铁器行的产品。这些人强调,邓名对四川木材、铁器生产的关心并不在盐业、船业之下,更多次亲切慰问过各个商行,指示他们一定要尽快拿出更多的发明、申请更多的专利。
众人在知府衙门里大叫大嚷了半天,全力挥舞着邓名的各种指示,如同挥舞着宝剑一般,向竞争对手身上(包括袁知府)用力刺去,最后袁象不得不承认场面完全失控,什么协议也休想达成——除了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袁象决定缩短叙州同秀才的考察时间。只要山西人肯留在叙州工作而不是去成都,那就可以由东家作保,预缴一些税金,在半年内获得同秀才的身份,从而享有一切功名特权——这毫无疑问是对政策的公开违背和擅自修改。但刚才高喊邓名指示,把嗓子都喊哑了的一群商行老板,此时却表示了对袁象知府英明决策的无条件赞同,还有人表示应该把考察期缩短为三个月,如果东家肯多交保金甚至可以进一步缩短。总之,任何能说服山西人留在叙州的政策都是好政策,哪怕是公开和邓名指示对着干的政策也英明得不得了。
幸好袁象还记得他的官职是邓名给的,不能让长江提督下不来台,所以顶住了压力,仍坚持考察期不得短于半年。
上午没有吵出结果,中午大家顾不得吃饭继续吵。经过短暂的修正后,袁知府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威严受到了同秀才士人的挑战,就再次坚定起来,表示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农业生产。最后见到无法以理服人,袁象就表示,既然诸位老板都有过在川军中的军旅生涯,那就干脆以武人的荣誉来解决纠纷——简而言之就是单挑。
刘知府享有打遍成都无敌手的美名,老板们都知道刘晋戈总是能靠这招达到目的,眼前的袁知府虽然没动过手,但大家早听说他是将门子弟,曾是邓名近卫队中的一员,别说单挑,这帮辅兵出身的商行老板二打一都没有胜算;消息灵通的人甚至知道袁象曾经和周开荒在邓名眼前演武过,据说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周少校都只能和袁知府打个平手,那老板们上去显然是白给。
单挑就是白挨打,然后在政策上任人宰割,商行老板们坚决不肯上当。邓提督还有一个备用方案,那就是向提刑衙门申诉。不过大家知道提刑官都是袁知府的旧部,上午袁知府还拍着胸脯保证,修改同秀才观察期的政策,一定能够得到叙州提刑衙门的赞同。既然提刑官在袁知府指使下连邓名的政策都敢改,那和袁知府本人打官司的下场可想而知。
于是老板们纷纷主张用团体赛取代个人赛,本来有人想提议五人组规模群殴,但掂量一下袁知府强大的个人实力,这个方案肯定也是自取其辱;十人组似乎还是没有什么把握,百人组武斗看起来比较公平,不过这估计真能打死人。
而袁象坚决反对多人赛,脑袋一摆大发官威,要不就按他说的办,要不就上来单挑——那还是按他说的办。
把众位老板从困境解救出来的是邓名新送来的一个命令。信中称,由于战局完全出乎意料,所以要叙州紧急动员,征召更多的士兵和民夫到前线助战。
袁象捏着这封命令沉吟了一下,缓和了口气,和在场的老板们商议起来:“提督要更多的援兵,其中对我们叙州的要求并不高,因为本来我们叙州的人丁就没法和都府比,所以提督只要我们叙州设法动员一两千人就可以了,而要都府出动两、三万人。若是如此的话,后面再来的俘虏势必都要被成都要去,我们再截流的话都府肯定会抗议,而提督也不会不管。”
“还会有多少俘虏?”一个老板问道。
“可能还会有七、八万吧。”袁象简要介绍了一下军情。
“七、八万!”
老板们顿时眼都红了。叙州现在只有不到三万人口,就算把前一批的一万多战俘都留下来,也就是增加三分之一的劳工。
这么多战俘都归叙州所有不太现实,就算袁象和商行老板们肯冒险,邓名也绝对不会同意战俘人口在叙州占有绝对优势,叙州只能希望再留下二万战俘。若是想达到这个目的,那叙州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没用多长时间,包括盐商在内的全体与会者就一致同意大规模减产,叙州全面动员支援朝廷剿匪,出动一万五千士兵和民夫支援前线。
大家都同意按照动员比例来分配战利品,如果食盐产业能够提供五千士兵和民夫,那事后就应该将三分之一的战俘划拨给食盐产业。而袁象则要求采用抽税制来满足农业需要,他表示无论哪个行业,他都要抽百分之五十的税,也就是说如果盐业分到了五千俘虏,那有两千五百就得成为屯垦的自耕农。
这个税率又引发了新一轮疯狂的争吵,而袁象发觉此刻他无法靠单挑来威胁诸位老板了,因为没有老板们的配合,他无法完成这样高强度的动员。靠武力强行通过税率的话,心怀不满的老板们肯定不会配合动员;而老板们虽然不愿意纳税,但也清楚如果没有知府衙门协助,那最后大家谁也别想拿到好处——他们不但需要袁知府篡改邓名的政策,需要知府衙门出面拉拢俘虏头目,还需要知府衙门出面顶住成都的压力。
税率最终定为三成,适用于已经送抵叙州的那一万二千战俘。协议达成时已经临近黄昏,而袁知府和老板们已经全都精疲力竭。虽然身心俱疲,但老板们都表示他们用不着休息,立刻就去安排全部的掌柜从事战争动员,一定要尽快向前线输送兵力。邓提督一向赏罚分明,叙州这样卖力,他不可能拒绝叙州对战利品的要求。
现在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成都的抗议,老板们担心袁象扛不住他铁哥们的压力,让大家白辛苦一场。
袁象不得不当众表示:“如果刘知府一定要我们交还战俘,本官会和他决一雌雄!”
“啊。”虽然袁象的表态很令人安心,但刘晋戈打遍成都无敌手的名气还是让大家有些担忧。
面对此种疑虑,袁知府傲然一笑,全身上下散发着强大的自信:“那是因为本官从来没有出手过。”
一整天的争吵和讨价还价,秦修采始终冷眼旁观。丁口在叙州还是在成都纳税,秦局长感觉对他来说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会议结束返回驿站时,幕僚们开始议论纷纷,他们都觉得袁象和刘晋戈的关系那么好,似乎不太可能为了商行老板而撕破脸。
“事关上万劳力,就算不撕破脸单挑,大吵一架估计是免不了的,这可都是税源和兵源啊。”秦修采笑呵呵地说道。
“刘知府和袁知府可是刎颈之交啊。”一个幕僚忍不住说道。
“呵呵,陈余和张耳也是刎颈之交。”秦修采又是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