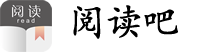汉水位于豫南与鄂北交界处,北岸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南边却横亘着一片绵延不绝的丘陵。北方气候寒冷,目前虽已是初春时分,枯黄的树梢尖上都冒出一茬茬绿嫩的幼芽,但隔冬不化的积雪仍在这北国大地上铺起了一层素裹银装。
夕阳西坠,古道苍茫。夹杂着冰粒的狂风又开始肆虐,漫山遍野的草木簌簌作响,积在树梢的残雪纷纷坠下,随风飘至半空,又被卷入冰冷的河水中,天地间一片混浊,显得分外萧索。暮色四合,浓云如墨,这种萧索的感觉,也随着这夜色而越发浓厚了。
汉水近岸处仍是冻结,变得狭窄只有十数步距离宽的河道上,疾劲的江水夹杂着大大小小的碎冰块奔流直下,击撞出惊天动地的咆哮声。
江北岸边遒劲有力地矗立着一株的百年老槐,那老槐不知有多久的年代,粗达丈余,四五个大汉也合抱不过来。树下立有一面石碑,上面刻着三个龙飞凤舞的草体大字:仙人渡。由此处渡过汉水后,南岸便是襄阳城!
不过此处这里虽有渡口之名,却是不见桥梁与渡船。原来此地本因与襄阳古城隔岸相望,旧名“望襄渡口”,通连着由京城直达岭南的官道,建有木桥以供车马通过,后因河道狭窄,江流湍急,洪水数度冲毁木桥,当地官府便改由数里外重建渡桥,此地便废置不用,反却成了一些私贩者搭船偷渡之处,改个名字叫做“仙人渡”,意是江水劲疾,又无渡桥,只有用仙法或能渡河无虞。
在此初春寒冷之际,江岸边少有行客,渐显荒凉。但在这行人渺渺、寂静已极的薄暮中,在那汹涌湍急的汉水河心中最狭窄处,却有一叶孤舟在当中飘摇不定。
更奇怪的是那小舟虽处在万马奔腾的江水中,却犹若中流砥柱般稳稳不动,仿佛有一只无形绳索牢牢拉住船底。看似在急涌的江水中晃荡不休欲要沉没,却几度履险若夷,从浪尖水底中钻了出来。
小舟中赫然有一人,头顶蓑笠,铁衣及膝,手持钓竿,沉腰坐马,竟在这乱石横滩、生死天险的江心中悠然垂钓!
忽有夜鸟惊起,远处隐隐传来马嘶声。片刻间,两骑沿杂草丛生的小道如飞驰来。当先是一匹黄马,骑者一身仆从打扮,身着青衣,头扎纶巾,身材修长,面目姣好,虽只是一个小书僮,眼目顾盼之间,宛如利剪,其中还透着一份俊秀华美的气度。那匹马儿蹿行甚快,嘴角已喷出浓浓的白沫子,一望而知是急赶了远路;第二骑是匹浑身纯白不见一丝杂色的白马,马上人穿着银白色的长衫,一派悠闲雅儒的文士相貌,就像一个赴考的秀才,腰间插了一支翠绿长笛,唇边还隐约可见两个小小的酒涡,甚是讨人喜欢。只是他眉心紧皱,似是正在苦思冥想中。
不问可知,这化装成游山玩水秀才模样的主仆二人正是人称“浪子杀手”的苏探晴与摇陵堂舞宵庄庄主林纯。
他两人在洛阳城外与擎风侯分别后,一路上由摇陵堂金锁城主安砚生带着数百侯府亲兵护送,浩浩荡荡好不威风。苏探晴与林纯皆对这等排场十分不习惯,几度催安砚生先回洛阳,安砚生却推说身怀擎风侯之命坚拒不允。苏探晴知道擎风侯有意如此大张旗鼓张扬其事,好让江湖上都知道他出使炎阳道,纵然炎阳道有所防范,至少按江湖规矩不会于半路上公然下手。何况擎风侯既然施计令卫醉歌与司马小狂等人从侯府中劫走假顾凌云,无非是想借此机会找出七色夜盗与卫醉歌的落脚处一网打尽,亦绝不会让他乘隙回洛阳通知司马小狂等人,而且就算他能暗中潜回洛阳,一时三刻也未必能摆脱擎风侯的监视联络司马小狂……所以苏探晴纵是担心卫醉歌与司马小狂的安危,却只好暂时放下这个念头。他只道必是林纯给擎风侯通风报信,想到还与自己勾指为誓,更是对她暗生怨意,一路上的态度十分冷淡。林纯冰雪聪明,如何看不出苏探晴的冷漠,可她本就是心性高傲,当着安砚生的面更不屑找苏探晴问个明白。
其实他两人间本无什么矛盾,只是苏探晴元宵节灯会那日在洛阳城中惊艳一见后,已不知不觉中对林纯暗生倾慕,可事后才知道她竟就是摇陵堂中的舞宵庄主,而苏探晴心目中早将顾凌云的杀父仇人擎风侯视为大敌,加之摇陵堂在江湖上声名不佳,他对摇陵堂中人皆怀有一份潜意识中的反感。心中迁怒于林纯,也不问个清楚便将通风报信的罪名加在她的头上,再看到敛眉夫人执意让林纯与之同行金陵,更是认定她与擎风侯夹杂不清的关系,既是痛惜她不能洁身自好,心中又暗地里偏偏禁不住浮想联翩,这等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态让他浑若变了一个人,面对林纯时再不见往日的潇洒从容,反是总在不经意间挖苦几句;林纯本对苏探晴颇有好感,但她向来被人宠信惯了,又何尝受得了苏探晴这般的冷落,吃几个没趣后亦不再理睬苏探晴。这一路行来,两人关系越来越僵,形同陌路,若无必要连话也不肯多说一句。
安砚生护送苏、林两人走了二日后,眼见将到了武当山附近,已接近炎阳道的势力范围,方才带兵返回洛阳复命。同时按擎风侯的命令订下疑兵之计,先派两个身材相貌与苏、林二人十分相像的士卒由官道上往金陵而去,苏探晴与林纯则化装成秀才与书僮,由小道往江南进发。
苏、林二人一路上隐踪匿迹、星夜兼程,到了这仙人渡时已是夜幕时分,人困马乏,计划连夜渡过汉水后在襄阳城中打尖休息。
两匹马儿来到汉水岸边,面对奔流的江水停下步来喘息。林纯眼望四周,目光停在那江心中的小舟上,顿觉蹊跷。她本是一路上与苏探晴赌气,此刻看到那江中垂钓者也顾不得许多,故意提高声音道:“公子啊,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我看这渡口似是荒废已久,如何渡江?”一面又放低声线:“那个小船上的人颇古怪,恐怕有些麻烦。”
苏探晴早注意到那江中小舟,暗中运功看去,只见那铁衣人在飘浮不定的小舟中稳若磐石,一付安心垂钓不管身外事的模样。那钓竿仅露在水面上的部份就足有二丈余长,也不知是什么材料所制,黑黝黝的似极沉重,可那铁衣人却行若无事地挥洒自如,只是一双执着钓竿的手臂筋骨毕露,显是臂力极强。他头戴一顶宽大的蓑笠,根本瞧不清楚面目,只看得到他颌下几缕青色长须在风中飞舞,年龄应该不小。
苏探晴暗暗心惊,此人毫无来由地出现在这天险绝地中,偏偏又如此悠闲,显然是有备而来。此地已处于炎阳道的势力范围中,按理说从上月起先是刘渡微将炎阳道盟主“侠刀”洪狂的首级送至摇陵堂,接着炎阳道二护法顾凌云又失陷洛阳,虽然擎风侯严令封锁消息,但江湖上早是谣言四起,炎阳道绝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可这段时间里先有司马小狂夜盗洛阳十数家巨户,又有卫醉歌当街挑战擎风侯,炎阳道却并没有什么行动,可谓极不合情理。以炎阳道素来的作风,不动则已,一动必是雷霆万钧之势!
苏探晴心中思索,面上却是若无其事,对林纯笑道:“木儿莫要心急,你看那江中不是有一只渡船么?快快将那船家唤来。”两人早就说好,苏探晴化装为秀才,以名为姓,化名“秦苏”,而林纯则扮作是苏探晴的书僮,将“林”字拆开,便以木儿相称。
林纯装模作样对那铁衣人大喊:“那位船家,我们要渡河,你快将船儿靠到岸边来。”
江风疾急,早将二人的话吹入那舟中铁衣人的耳中,他却浑若不闻,仍是一动不动保持着那垂钓的姿势,仿佛千年石像一般。
苏探晴细察四周形势,这一段河道狭窄,以他与林纯的武功策马跃过应该不是难事,只是那船上的铁衣人形貌不俗,贸然显露武功实为不智,沉住气大叫道:“船家且莫生疑,我们主仆二人由京城去江南游玩,只因迷路错过了宿头,今晚必得要赶入襄阳城中。只要你将我主仆二人载渡过江,定会多给你些船钱。”
那铁衣人嘴角似是微微牵扯出一分笑意,却仍是一动不动,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那钓竿。
林纯眨眨眼睛,用足令那铁衣人听到的声音对苏探晴道:“公子可别怪木儿多嘴,听说这一路上不怎么安全,时常有强人出没,我看这船家有些古怪,我们可不要遇上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强盗了。”
苏探晴装作急声道:“这可如何是好?还不快快绕道而行。”
林纯道:“可眼见天就全黑了,也不知这附近何处才有渡口,若是不能在今晚赶到襄阳城中,我们主仆二人岂不是要露宿荒野了么?”
苏探晴跺足道:“露宿荒野总比落在强盗的手里好些,还不快走?!”他料这铁衣人若是敌人,定是专门在此等候,绝不会任由两人离开,所以这般说以试探对方。
果然那铁衣人举起手来对二人打个招呼,示意稍等,却仍是不发一语。
林纯对苏探晴挤挤眼睛:“这个船家莫不是个哑巴?”
苏探晴摇首道:“木儿不要乱说话。我看这船家能将小船儿停在如此凶险的地方垂钓必有其缘故,倒不如先等他一会。”
林纯一指那老槐下的石碑:“公子你看,这个地方原来叫做‘仙人渡’。嘻嘻,那河岸最窄处不过十余步宽,不如我们放马冲过去,也学学这仙人凌空飞渡。”
江面最狭窄处正中便是那垂钓的铁衣人,若是依林纯之言,他们必要从那铁衣人的头顶飞过去。苏探晴知道林纯有意试探那铁衣人,接口道:“如此倒不失一个好办法,就怕马儿力乏,若是掉到河中,这大冷的天可不是好玩的。”
林纯笑道:“我身子轻些,应该可以冲过去,要么我先试试,公子随我后面就是。”偷眼看那铁衣人,仍是万事不萦于怀的样子,对两人的说话充耳不闻。
苏探晴心想若是与这古怪的铁衣人过多纠缠只怕有变,倒不如速战速决,缓缓点头道:“也好,木儿你小心些。”手中握紧玉笛,盯紧那铁衣人,防他突起发难。
林纯策马退后几步,大喊一声:“船家小心,我可冲过来了。”她艺成后少遇强敌,虽看这铁衣人臂力不弱,却也未放在心上,反是跃跃欲试。马刺轻扎座下踯躅不敢前行的黄马,直冲过去。
谁知林纯策马刚刚奔出几步,忽见河心那铁衣人猛然一提手腕,黑色钓竿破水而出,竟是足有三丈余的长度,一挥之下在空中兜个圈子,看是寻常挥杆,钓丝却不偏不倚地朝着林纯旋来。铁衣人本是静若石像,这骤然一动却是犹若脱兔,黄马的马蹄刚刚踏在结冰的河岸上,足下生寒又经此一吓,蹄下一软已陷入冰河中,速度立刻缓了下来。林纯骑术虽精,却也未料到此突发情况,腰腹用力一夹,想把马蹄从冰河中拔出,但马儿受惊下已是不受控制地人立而起,眼见那钓竿就要击在林纯的头上,林纯口中轻叱,右手往头上轻抹,已将簪在发间的巧情针拔了出来,往那钓竿上搭去……
苏探晴心中震惊。他身为杀手,对于出招时机最为讲究。铁衣人蓦然发动掌握的时机绝好,正在林纯坐骑将渡未渡之际,而且算好了林纯渡河时定有防范,所以采用惊马之策,立刻让林纯陷入被动之中,虽仅是半招已可瞧出这位铁衣人在武学上不凡的造诣。苏探晴不及思索,身形已如烟般掠出,一掌按在林纯座下黄马背上,将惊跳起的黄马按落,手中玉笛亦往那长长的钓竿迎去。
铁衣人的钓竿却是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一荡即回,似是根本就无意朝两人出手。苏探晴的玉笛与林纯的巧情针都迎了个空,连忙退开几步,好避开那长长钓竿的攻击距离。
铁衣人微微摇头一叹,似是自言自语般喃喃道:“这两个娃娃功夫好得出奇,竟然会嚷着怕什么强盗,可真是天下大奇了。”
苏探晴与林纯互相交换一个眼神,皆是大生戒备:这铁衣人出手自然,不落丝毫斧凿痕迹,却已迫得两人都不得不显露出武功来,无疑是位难以对付的高手。
那铁衣人长长的钓竿上竟不设钓钩,更无鱼饵,却挂着一只模样奇怪的小动物。那小动物体型似狗,面相似鹰,嘴上长着一张尖喙,从水底钻出浑身竟是没有一点水渍,不停发出“吱吱”的叫声,口中还嚅嚅而动,似是刚刚将什么东西吞入肚中。在空中猛一弹身,已从钓竿上落下,闪电般飞钻入铁衣人的怀中。
“哇!”林纯惊魂稍定,不由又发出一声惊呼:“那是什么东西?”
铁衣人微抬起头,从蓑笠下露出一对眯缝着的眸子,只见他刀眉细目,丰鼻阔口,皱纹满脸,也不知有多大年纪,一张铁面上隐隐浮露出沧桑之气。他抚着怀中那小动物的头,嘿嘿一笑:“它名叫小风,乃是我养的小宝贝。”他语音苍老,却是中气充沛,一股低沉的声音撕破寒风直抵苏探晴与林纯的耳中。
林纯奇道:“小风,这名字好可爱。不过大叔把它放在水底下做什么?这么冷的天气,也不怕冻坏了它么?”
铁衣人漠然道:“小风才不怕水,刚刚不过是到水下是吃一顿晚餐罢了。”随着他的说话,那只小动物从他掌指间探出头来,两只灵动的圆眼睛望着林纯,骨碌骨碌转个不停。
纵是大敌当前,林纯也忍不住拍手大笑:“好可爱的小家伙。难道还会自己下水捉鱼儿吃?大叔你能不能卖给我?”她少女心性,此刻见到这长相可爱名唤小风的小动物,竟与这不知是友是敌的儿铁衣人攀谈起来。
铁衣人道:“你这女娃娃倒是颇有礼貌,只凭这一声大叔,若是喜欢,老夫便送与你又何妨?”微微一顿又古怪一笑:“就只怕你养不活它。”
林纯大喜:“大叔你放心,我保准不会饿着这小家伙。”随即醒悟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女子?”
铁衣人冷然道:“老夫若连你这等三流的装扮都看不出来,岂不白混几十年的江湖?”
林纯不服气地哼了一声:“大叔既然专程在这里等着我们,自然早就知道了我们的来历。”
铁衣人眼中精光一闪:“胡说,老夫岂会专程等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娃?”
林纯一撇嘴:“就算大叔眼力好些,又何必这么倚老卖老?更何况,瞎子也看得出天下怎会有我这么可爱的小书僮,自然是女孩子扮的……嘻嘻。”说到最后,自己忍不住先做个鬼脸,笑了起来。铁衣人听得啼笑皆非,原本冷冰冰的面上亦是闪过一丝笑意。
苏探晴见这铁衣人口气极大,情知遇见了前辈高人,拿不准他意欲为何,只得以言语试探,恭敬道:“前辈请了,我们正欲赶去襄阳城中,不知可否借船一渡?”
铁衣人重又板起了脸:“你这两个小娃娃功夫不错,若是要渡河也用不上老夫的小舟,这便去吧。”手中钓竿往江底微微一撑,小舟立时逆流移开几尺,让出路来。
苏探晴与林纯对视一眼,目中皆流露出一丝惊惧。那钓竿虽似是精钢所制,毕竟长达三丈软不着力,可这铁衣人却仅以一撑之力便使小舟在这急流中逆行向上,而且浑若无事不费半分力气,平生所见之人中武功高到这种地步者实在寥寥可数,便是杯承丈与擎风侯似亦没有这等举重若轻的造诣。铁衣人虽已让开路来,他二人却是谁也不敢在这样的高手面前飞马过河,若是铁衣人趁他们凌空悬虚时出手一击,只怕连一招也接不下来。
铁衣人看二人踌躇不前,一瞪眼睛:“两个小娃娃还不快走?”
林纯转转眼珠,偏头一笑:“江水寒冷,大叔莫要着了凉。”
铁衣人似是看出了二人的心思,冷笑一声:“两个小娃娃尽可放心,老夫何等人物,岂会对你们行偷袭之事?”
林纯脸上一红,犹不肯服软,正要再说,苏探晴一把拉住她,对铁衣人拱手一揖:“前辈既在此处现身,可是有所指教?”
铁衣人道:“你我素不相识,哪有什么指教?老夫不过是给小风喂食,你们要渡河就快走,莫要多罗嗦。”
林纯插言道:“大叔刚刚不是说愿意将小风送与我么?为何又说我养不起它?”
铁衣人哼一声道:“你这女娃娃说得轻巧,可知小风平日吃些什么食物?”
林纯眨眨眼睛:“不过是些鲜鱼活虾,有什么了不起?”
铁衣人拍拍那小动物的头,肃容道:“可惜小风从不吃鱼虾,最喜吃活猛的毒物,你可有办法天天喂它么?”
林纯吃了一惊:“大叔你若舍不得送便明说好了,何必吓我?”
铁衣人哈哈一笑:“你道老夫为何会来这汉水中?只因这初春时节,那最生猛凶狠的毒虫方可从冬眠中醒来觅食,小风刚才这顿美餐便是一条可令人顷刻毙命的五步蛇。”
林纯犹是半信半疑:“大叔你莫要骗我,这么点的一个小东西,如何可在这江底下找到毒蛇,岂不比大海捞针还难?”
铁衣人笑道:“你莫小看我这宝贝,它的鼻子最灵,越是剧毒越是嗅觉敏锐,刚才便是闻到了那只毒蛇的气味,这才拖着老夫一路到这汉水边上来。”
林纯摇摇头:“我刚刚分明看得清楚,它嘴里吃的东西可不是一条蛇。”
铁衣人傲然道:“小风岂会囫囵吞食?它只吸取毒虫体内最精华的毒液,刚刚吃在嘴里的不过是那条五步蛇的蛇胆罢了。”
苏探晴忽曼声长吟:“曲罢一尊空,飘然欲驭风。我曾看过一本《奇兽录》,里面记载着一种名为驭风的上古神物,据说专以毒虫为食,是天下毒物的克星,莫非就是它?”
铁衣人面露惊喜:“不错,此物名唤驭风麟。想不到这位小兄弟如此博闻,竟然知道我这宝贝的来历。”
苏探晴谦然一笑:“那书中还记载道此驭风极有灵性,虽以毒物为食,身挟天下至毒,却从不以毒为祸,而若是养它的主人心怀不轨意图用毒害人,则必会遭驭风反噬……”
林纯瞪大眼睛盯住苏探晴,似是第一次见到他一般:“我从未听过这些事情,你又怎么知道?”
苏探晴哈哈大笑,装出一副穷酸秀才样,摇头晃脑道:“所谓读万卷书胜行万里路,古人诚不我欺也!”又对林纯眨眨眼睛,故作神秘道:“木儿放心吧,此等神兽惟有德者可居之,这位前辈既能收养这驭风麟,定是心怀坦荡之士,断断不会是强盗了,我们只管放心过江。”这番话却不是胡言乱语,苏探晴师从杀手之王杯承丈,对用毒之术颇有研究,加上他生性好学博闻强记,这些年有时间便四处收集天下古籍奇书,所以才一下便想起了这驭风麟的来历。他虽不知这铁衣人的来历,但看他一脸凛然风范,又深信那《奇兽录》中对驭风麟的描述,不知不觉中敌意大减。
林纯分不清楚苏探晴言语中的真假,那铁衣人却是击掌大笑:“想不到老夫遍行天下,今日却无意中遇见一位知音。来来来,老夫这里还有一壶好酒,可与小兄弟同享。”说话间从怀中取出一只精致的酒壶,先仰头喝了一大口,再对着苏探晴掷来。
铁衣人掷壶之势并不很用力,酒壶旋转着缓缓飘来,仿若下面有只无形的手托着一般。苏探晴伸手去接时那酒壶却蓦然一沉,竟是接了个空。眼见酒壶就要摔在地上,忽又一弹,往铁衣人的方向回旋而去。
那铁衣人哈哈大笑:“只不过想喝到老夫这壶酒,还需要瞧瞧小兄弟的本事。”原来那铁衣人一掷之力看似简单,其中却附有极古怪的内力,于平掷之力中隐含一份回挫的力道,也不知他是有意无意,露了这一手极上乘的武功。
幸好苏探晴早有防备,右手甫一接空立时左足反踢,拧腰一个旋身,左手由下至上一捞,已重将那酒壶接在手中。但觉那酒壶上依然有一股大力旋荡不休,用足腕力方才握紧,苏探晴淡淡一笑:“多谢前辈赐酒。”不假思索地张口就着壶嘴饮去。
林纯本想提醒苏探晴提防酒中有毒,却见苏探晴已是毫不犹豫地几大口美酒下肚,闭起眼睛似是回味那壶中美酒的滋味,半晌后方长吐一口气,清吟道:“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这是诗经中《柏舟》的句子,用在此处确是恰到好处。
铁衣人见苏探晴以极快的应变接下酒壶,眼露欣赏之意,以掌击船舷与其吟声相合:“想不到小兄弟果是文武兼修,此酒乃是近百年的窖藏,确配得上这一曲古风!却不知可合小兄弟的口味?”
苏探晴又喝了一大口酒,点头道:“此酒入口绵长,回味无穷,真是好酒。只可惜晚辈并不通酒道,若是晚辈的一个朋友喝到了前辈这壶美酒,定有一番妙论。”他本是天性爽直率性之人,这些日子在洛阳城中处处提防隐忍,不敢以真心示人,直到这一刻方借着微涌酒意流露出一些本性来。
铁衣人欢声大笑:“老夫活了一大把的年纪,只好品酒、听曲、垂钓、习武四件事。看这位小兄弟面相端正,言语不俗,想必那位好酒的朋友定也是个妙人,却不知如今在何处?”
苏探晴扫一眼旁边目瞪口呆的林纯,苦笑一声:“前辈容晚辈卖个关子,先不说出那位朋友的名字。他日若有机会,倒真想陪他一起与前辈痛饮一场。”仰头又灌下几大口美酒。原来苏探晴心中所想到的人却是前几日在洛阳城匆匆一见的卫醉歌,他欣赏卫醉歌光明坦荡的气度,虽仅仅初识,在心中却不觉已当做莫逆之交。只不过在林纯的面前,苏探晴却不方便将卫醉歌的名字说出来。
铁衣人也不追问,语中却大有深意,淡淡道:“我看小兄弟亦是个性情中人,倒不若陪老夫在此汉水边上饮酒吟诗垂钓为乐,何必去那红尘乱世中争执名利?”
苏探晴似已有三分醉意,狂态微萌:“晚辈此去江南,无非是要在那十丈红尘中寻一份宁静胜景,岂不闻‘千锺尚欲偕春醉’,前辈又何苦要留下晚辈呢?”
铁衣人料不到引来苏探晴这番说辞,放声豪笑:“好好好,好一句‘千锺尚欲偕春醉’,今日老夫且与小兄弟共谋一醉。”蓦然手腕一抖,钓竿挥处,黑暗之中只见一道微白的光芒电射而来,却是以钓竿上连结着的长长钓丝缠向苏探晴手中的酒壶,欲将酒壶从苏探晴的手中卷出。
苏探晴本能一转身避开钓丝,童心大起,微笑道:“区区一壶美酒如何够二人分,前辈不若就忍痛割爱吧。”仍是大口灌酒不休。
铁衣人不怒反笑:“好小子,老夫便不信夺不下这壶酒。”钓竿反拨,钓丝在空中划几个圆圈,重又往苏探晴的手腕上缠去。
林纯见铁衣人虽是含笑出手,但招数精妙,出手迅捷,那钓丝虽是细小,挥动中却带起呼呼风声,使得像是一套鞭法,看样子若是击在苏探晴身上,立时便会皮开肉绽。侧身挡在苏探晴面前,口中尚笑道:“大叔莫要生气,我家公子见到美酒就舍不得丢下了。”
铁衣人惊道:“你这小女娃子还不快闪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不知林纯亦是身怀高强武技,只恐误伤了她,钓竿去势立缓。
林纯似是对刚刚铁衣人夸奖苏探晴颇不服气,嘴里轻哼一声:“我不妨与大叔打个赌,若是大叔在我家公子喝完壶中酒之前还不能抢下这壶酒,便将那小风送与我如何?”她知道那铁衣人身处江心,难以近他身畔,又以三丈余长的钓丝出击,可谓是立于不败之地,虽然他对己方未必有恶意,却不知到底有何意图,以她与苏探晴二人联手亦未必能讨得了好。不过林纯冰雪聪明,料想此铁衣人纵然是武功高绝,但那钓丝由远距离伤人容易,想要抢下一个小小的酒壶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方出此以己长攻敌短的激战之法。
铁衣人经林纯一激,也不动气,放声大笑:“便如此说定了。若是老夫抢下了这壶酒,你两个小娃娃可要答应老夫一件事情。”钓竿再挥,钓丝在空中旋了几个圈子,这一次却是往林纯的腰侧卷来。那长长的钓丝也不知是何材料所制,细长柔韧,在铁衣人的内力催动下十分灵活犹若臂指。
林纯不敢怠慢,巧情针织成一片针网,严密防御,再瞅准钓丝的来势,使一招“嫦娥奔月”,半尺长的银针先回勾再弹出,直往那钓丝上挑去。她的巧情针本就走得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的路子,与铁衣人钓丝中隐含的鞭法各擅胜长。
铁衣人朗然一笑:“看不出你这女娃娃竟有这么好的身手!唔,能将公孙一脉的织女针法能练到如此收放自如的地步,除了差些火候,恐怕与公孙映雪亦不分上下了。”他口中说话出手却不见丝毫放慢,手腕一沉,那钓丝本是十分柔软,却忽如长棍般抖得笔直,与巧情针硬碰一记。
林纯被铁衣人一口道破了来历,震惊不已,尚不及思索,又忽觉一股大力由针上直传而来,虎口一麻,巧情针几欲脱手,心头大骇,料不到这铁衣人的内力如此霸道,竟能强行隔空传劲。钓丝已趁她针法微乱的空隙逸出针网,仍是缠往苏探晴的手腕。
钓丝似缓实急,来势极快,苏探晴只顾着仰头将酒倒入口中,似乎根本未见到袭来的钓丝。眼见钓丝就要缠在他手腕上,刹那间却见他猛然屈膝弯腰,仍是保持着饮酒的姿式,身体却已矮了一截,已从钓丝底下钻过。
谁知那钓丝在空中犹如活物般蓦然下沉,直往苏探晴的头顶击下。苏探晴却似早有意料,脚下急退三步,钓丝堪堪从脸前掠过。这次闪避胜在时机掌握得极好,正是铁衣人招法用老不及变力之际,更是算准了钓丝长度,钓丝与鼻尖只差了半寸的距离,当真是险到毫巅。
铁衣人赞了一声:“好!”深吸一口气,内力到处,骨骼一阵喀喀响动,已然伸直的手臂竟然又暴长数寸。
苏探晴料不到这铁衣人竟能无中生有使出这一招,变起不测下闪躲不及,原本无法再前进的钓丝已缠在他的右腕上。苏探晴右肘往下一曲,宛若无骨般绕了半个圈子,从钓丝中脱开。但饶是他闪避得快,脉门仍是轻轻一麻,被钓丝尾端轻轻勾中,指尖不由一松,酒壶已被钓丝卷走。
苏探晴变招极快,轻喝一声,左手已一把抓在钓丝之上,食、中、无名三指弹出,濯泉指连发,但觉钓丝上所附内力雄浑无比,左手已被弹开,但那钓丝上的力道亦被他三记指风化解,去势顿缓,苏探晴右掌已循隙直进拍在酒壶上,而铁衣人的钓丝复又反卷回,亦缠在酒壶壶耳之上。恰好林纯的巧情针业已刺到。飞行在空中的酒壶微微一滞,经不起三人内力的夹击,“啪”得一声,竟爆裂成无数碎片。
这犹若电光火石的几下交手不过刹那的功夫,铁衣人虽是武功高绝,又凭着钓竿以长击短,但在苏探晴与林纯的联手之下,却也未能占着丝毫便宜。
苏探晴与林纯皆是心中狂震,这铁衣人不知是何来历,他二人各施绝学联手与之相斗,也不过勉强算个平手。纵然是擎风侯亲临,亦没有这等高得不可思议的武功。
铁衣人愕然望向苏、林二人,唇边忽露出一份神秘的笑容:“不错不错,果是英雄出少年!只是可惜了这一壶好酒。”
林纯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拍手笑道:“大叔输了,快把小风给我。”要知她与铁衣人相约趁苏探晴饮尽壶中酒前夺下酒壶,如今酒壶已碎,双方最多仅可算为平手。林纯如此强辨已可说迹近无赖,料想这等前辈高人一招受挫,纵然未必肯将那上古神物驭风麟相赠,亦绝不会再纠缠不休。
铁衣人哈哈大笑:“你这女娃娃口齿伶俐,言辞锋利,却也未免太不讲道理了吧。也罢,老夫便让你二人过河吧。”铁衣人自重身份,当然不会与这小女孩一般见识。
林纯赧然一笑:“多谢大叔成全,却不知大叔怎么称呼?”
铁衣人双目一瞪:“老夫可问你二人的姓名了么?”言下之意自是不肯将身份泄露。
苏探晴想起刚才铁衣人的话,问道:“刚才前辈说若我二人输了,便要答应你一件事情,却不知是何事?晚辈不才,愿替前辈分忧。”
铁衣人正色道:“那不过是老夫一时之兴,不提也罢。倒是你二人这一去,只怕会引起江湖上的偌大风波,须得谨慎从事。莫要一时失足,留下了千古骂名。”
苏探晴听那铁衣人话中有话,心想擎风侯将二人出使炎阳道之事昭告天下,只怕自己的身份早已被他看出,拱手长揖,亦是一语双关道:“前辈尽可放心,晚辈心中自有善恶之念,绝不会做那千夫所指之事。”
铁衣人点头微笑道:“瞧你亦是熟读诗书之辈,当知善恶仅在一念之间,凡事皆要三思而行。老夫闲云野鹤的性子,向来也不愿意管江湖诸事,只不过不忍见无辜百姓受那刀兵之苦,方好言相劝一句……”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忽然严厉起来:“若是你一意助纣为恶,老夫绝不轻饶。”
林纯一挑眉,噘起小嘴:“大叔为何如此说?我们不过是去江南游山玩水,怎谈得上什么助纣为恶,又能引起什么江湖风波?”
铁衣人洞悉天机般一笑:“二个小娃娃这身打扮或可瞒得过别人,却瞒不住老夫的一双利眼。老夫言尽于此,此去江南风波险恶,你们好自为之吧。”
苏探晴听铁衣人如此说似是别有隐情,恭敬道:“承蒙前辈指点,小子谨记于心。却不知前辈意欲何往?若能同行,路上亦可多多聆听前辈教诲。”
铁衣人嘿嘿一笑:“若是有缘,自会再见。”说完这番话,也不见他如何起身作势,瘦削的身体蓦然由小舟中弹起,伴随着他一声长啸,跃过数丈稳稳落到对岸,竟就此朝着襄阳城方向扬长而去。
苏探晴与林纯料不到铁衣人说走就走,只见那一道身影如星丸跳跃,去势极快,不几下便消失在茫茫山峦中,夜风中仍隐隐传来他的长吟声:“凌云长啸,舒放愁肠结。人生易老,莫教双鬓添雪……”
二人面面相觑,回想这铁衣人的种种行事,疑云暗生。林纯忍不住对苏探晴问出心头的疑虑:“这个铁衣人武功奇高,到底是什么来历?他似乎已瞧破了我们的身份,可看样子又不像是炎阳道派出的高手……”
苏探晴长叹一声:“前辈高人,岂可以常理度之。不过我总有种直觉:此人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
林纯沉吟道:“不管他是不是炎阳道派来的高手,此地已是炎阳道的势力范围,而我们行藏已露,只怕那襄阳城中还会有些不可预知的变故。何况这铁衣人不是说什么此去前路风波险恶么,莫非炎阳道早已设下埋伏?我们是否应该换条路线?”
苏探晴豪气涌上,一把撕开前襟,任凭凛冽的夜风从脖颈灌入:“哪管前路有刀山火海,我也都要闯一闯。”转头对林纯哈哈一笑:“木儿,且随你家公子渡江去也。”也不待林纯答话,扬鞭策马,由汉水河上凌空飞渡而去……
一轮残月已不知不觉挂上中天,河水反映着清明月色,遍地银辉。
林纯望着衣袂飘风飞马渡江的苏探晴,再抬头看看那碧蓝澄澈不见半点混浊的天空,良久不语,似是突然被勾起了什么心事。她仿佛第一次发现:在这个外表文秀的年轻人心底,还有一份压抑许久的豪情血性,正随着他们未知的行程,一步步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