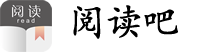欧青谨见夏瑞熙当真要去抱箱子,忍不住伸手按住她,斥道:“你傻了啊?没听说现在不能抬重物的?”
夏瑞熙不说话,只是望着他笑,他虎着脸说:“你要放在哪里?”
夏瑞熙凑过去:“这可是我留给我儿子闺女的,我想把它埋在院子里的某个地方,可是我不相信其他人,这个活儿只有交给孩子他爹做啦!你看怎么样?”
欧青谨不说话,却是把箱子放到了他身边。
夏瑞熙在买来的那堆杂货中寻出一叠油纸,另从床脚下取出一只早就准备好了的坛子来:“把金条放进这里面来,银票用油纸包起来,装在一只小花瓶里,用腊封死花瓶口,两样东西分开埋。”
二人把东西收好后,欧青谨仍旧把坛子搬到床下藏好,拿着那只小花瓶有些坐立不安:“这个东西埋在哪里好呢?会不会让人家知道?要是被刨了去,我怎么向岳父交待?”
夏瑞熙道:“我想到一个好地方,后院不是有口枯井吗?等会大家睡了,咱们把坛子吊到下面去,然后把那枯井给封了,等日后熬不下去了,再把它取出来。至于这银票,咱们就把它埋在一个花盆里,上面种棵花,天天放在眼面前看着。你看怎么样?”
“好。”欧青谨想了想,又从坛子里取出六根金条来,不等夏瑞熙问他,他就解释:“这东西都要深埋了,再想反悔拿钱的时候就很费力,轻易就不要再打开了。这个还是你拿着吧,藏也藏个方便取出来的地方。”
夏瑞熙听他这意思,竟然是除非实在不得已,坚决不会动用那笔钱了,心中大乐。笑得也就格外甜:“还是夫君大人想得周到呀。”不管她其他的嫁妆散去多少,这笔钱都是有保障的。
欧青谨哼了一声,低着头封坛子,又到处寻绳子。
夏瑞熙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拉过他的手臂抱在怀里:“还生气呢,这样小气的男人就没见过。”
欧青谨略微不耐烦地说:“怎么这么多话,别耽搁我做事,明日还要起早,我把你送回家去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
比如去夏家铺子里挨个儿的巡查一遍,看看可有什么人去捣乱,令庄子里加派人手,注意安全。夏夫人再厉害,到底也不好抛头露面的到处跑,家里还得有个主事的,这些外面的事情还是得男人去处理的好。
夏瑞熙笑道:“那你答应我,别生气了好不好?”
欧青谨闷闷地说:“我不喜欢你跟我解释的那种方式。态度很生硬,仿佛你不是你了。还有以后不许不信任我,要不然我再也不理你了。”
“好。我发誓再也不会了。”夏瑞熙偷偷在心里添了一句,那还得看你的表现,否则该骗的还是会骗。
欧青谨低声嘟囔了一句:“这么多的心眼,也不知道怎么长出来的……”
“什么?”夏瑞熙没听清。
“没什么,让你快准备睡觉了。等会儿还要起来给我把风呢。”
第二日一大早,欧青谨便让花老虎跟车,自己骑着马把夏瑞熙主仆三人一并送到了夏家。夏夫人就在前厅里候着,欧青谨问候过夏夫人以后,不及去瞧夏老爷,自己立刻带着花老虎和一队人高马大,膀大腰圆的家丁巡查铺子去了。
俗话说,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模样来,这样,无论是族人也好,下人也好,外人也好,才不敢轻瞧了夏老爷这一房去,同时,得到的助力也就会更多。要是还没怎么的,你这房人先就垮了,人家就算想帮你也不敢伸手。
夏夫人一看见夏瑞熙,先是两眼绽放出惊喜,接着又埋怨:“青谨也是个沉不住气的,明明让他不要告诉你了。”
夏瑞熙笑道:“爹和娘体贴女儿,可是女儿也牵挂爹娘。他要不告诉我,我才要生气呢。这个时候,就是能宽宽爹娘的心,也是好的。我瞧瞧爹爹和瑞昸去。”
娘俩携手往夏老爷屋里去,因见夏瑞蓓不在夏夫人身边伺候,夏瑞熙便皱眉:“蓓蓓呢?”
夏夫人脸上露出一丝安慰的笑容来:“昨儿夜里你弟弟发烧说胡话,一直都是她在一旁守着的,多亏她细心周到,瑞昸半夜里就退了烧。天亮我才让她去休息了。”
夏瑞熙心里总算是放心了些,“蓓蓓今年懂事多了。”
夏夫人轻声道:“自从孙家那事之后,像变了个人似的,乖巧沉静多了。昨日那姓赵的上门来闹腾,她还哭着说是她不好,拖累了家里。”
不管夏瑞蓓是真心还是假意,她能做到这一步,也算不错了。说起来,她又何尝不是一个可怜人,夏瑞熙叹了口气:“等会儿我去瞧瞧她。”
刚进了里院没多远,王氏气哼哼地带着一个穿粉色衣裙,娇滴滴的小媳妇迎面过来,见着了夏夫人就气势汹汹地道:“那个扫把星呢?你把她藏在哪里去了?害得大伯哥哥碎骨断腿,她自己却什么事都没有?你叫她出来!”
那个穿粉色衣裙的小媳妇就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我苦命的夫君啊。”
夏夫人气得半死,夏瑞熙沉了脸,丽娘轻声道:“这是三少爷新纳的小妾朝霞。原来是唱戏的。”
夏瑞熙冷声道:“大伯母,你这是要干什么?谁是扫把星?谁害得大伯哥哥碎骨断腿?你一大清早就带着这不知什么身份的人到我们这里哭闹,你不忌讳,我们还忌讳呢。”
王氏这才假装刚看到夏瑞熙,“哟!”的长长叫了一声,道:“我道是谁呢,原来是二姑奶奶回来了。二姑奶奶,以前我还道你的终身大事就是最难解决的了,如今看来,三小姐才是那命里带煞的扫把星,这是要闹得家破人亡才算了事啊!”
夏瑞熙道:“大伯母,任谁都知道大伯和三哥是去那见不得人的地方与人争风吃醋才被打了,怎么就和蓓蓓扯上了?你这样闹,实在是不讲道理!”
王氏脸一变,尖声道:“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今日一大早,就有人来说,就是因为你们害了孙家的人,所以才要敲断他们的腿!你们自己做下的缺德事,却要害得我们跟着倒霉。”
夏瑞熙寒了脸,一字一顿地说:“大伯母,你可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害了孙家的人?我们是指哪些?包不包括你们呢?”
王氏嚷嚷道:“自然不包括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做的缺德事?”
夏瑞熙冷笑道:“你不知?那你从何得知是我们做的?这个罪名一落实了,你以为你就讨得了好去?你不是主谋也是从犯,最起码也是个知情不报!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过堂挨板子呢?我劝你,还是谨言慎行的好。”
王氏愣了愣,再不敢提孙家的事情,如同一个乡村泼妇,嗨嗨连天地哭闹起来:“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这是招谁了惹谁了,害成这样?我的儿呀,孩子他爹呀,你们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跟着你们去了呀……”
夏瑞礼那小妾也跟着依依呀呀地哭起来。
夏夫人气白了脸,她也是一夜未睡,思前想后弄得心力交瘁,如今给王氏这样一闹,头就有些眩晕起来,靠在丽娘身上才算是勉强站住了身形。
夏瑞熙烦不胜烦,她小辈的身份不能吼王氏,便拿那小妾做文章。对着那小妾一声厉喝:“住口!你是什么人?也敢到我娘面前哭闹!给我打出去!”
纯儿先就上前去给了那小妾一个耳光,一口唾沫吐到她脸上:“什么东西?也敢在我们家少奶奶面前这样胡闹!”
王氏立刻止住了哭声,护住那小妾:“这是你三哥新纳的妾。她哭正是天经地义。”又指着纯儿骂:“你个臭丫头,也敢欺主?”对着纯儿的脸就要搧上去。
纯儿躲开,良儿冷笑道:“真是笑话了,奴婢们跟着姑奶奶离开家才几日,原来外面买来的戏子也是主子了。也敢到正经八百的夫人面前哭闹了,这西京城里可是独一份呢。”
夏瑞熙嘲讽地道:“大伯母,这事是您老欠缺考虑了,妾是什么?就连身边体面些的一等丫头都还比不上呢,不让她在三哥身边伺候,怎么还让她出来闹?丢的可是您的脸呢。”
丽娘给了两个粗使婆子一个眼色,那两个婆子上前去拉那小妾:“对不住啦,谁让你这么不懂规矩呢!”
这边的人要去拖,王氏身边的人不让拖,两下里乱闹起来。纯儿和良儿怕危及到夏瑞熙,忙把她扶到安全的地方,用身子护住她。
夏瑞熙头都焦大了,这是唱的哪一出?威风八面的夏老夫人此时也闷声不出,任由闹得这般不像话,夏夫人这日子,可也真难过。她给丽娘使了个眼色,今日不管怎样,都得趁着机会把王氏的威风给灭了,否则以后烦都烦死人。
其实夏瑞熙却是冤枉夏老夫人了,昨日事情一发生,夏老爷怕夏老夫人年纪大了,禁受不住吓,早就安排她去了家中相熟一间庵庙散心去了。老的不在,夏老爷又病倒,夏瑞昸还迷糊着,所以王氏才越发的有恃无恐。
花厅那边传来丫头的惊呼:“三小姐,三小姐,您要做什么!别乱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