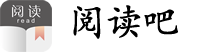虎蹲炮的射速不算快,射程有限,威力也很一般,称不上什么野战利器。现在汉八旗没有观察到明军有骑兵,欺负明军没有值得一提的远程武器,就把虎蹲炮拉到近距离上射击。汉八旗周围有王明德的披甲掩护,又有雄厚的兵力,不用担心明军反冲锋,倒是把虎蹲炮的威力提高了一些。但尽管如此,这些小型火炮的威力也就相当于大号霰弹枪而已,如果汉八旗使用的武器是排枪时代的野战炮,那么这种近距离的炮击就可以肆意地蹂躏明军的战阵,在一眨眼的功夫内把几百明军的阵地轰散。
可明军依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明军士兵大都是袁宗弟在夔东招募的,之前在军中别说火炮,就是火铳都没有见过几杆。看到清军一炮打来,被击中的同伴立刻重伤倒地,身上的盔甲完全起不到作用,这些留守的士兵都惊骇不已。对明军影响更大的是炮声,近距离射击的虎蹲炮隆隆作响,它们发出的爆炸声是这些明军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可怕的声音。
只有个别的军官因为参与过湖广的扫荡战,对火药发出的巨大声音有些心理准备,不过他们当时的心情也和现在不同,现在他们站在火药武器的对面而不是背后;而其他的军官都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前所未见的武器。
军官如此,士兵的表现就更不堪了,看到不断有同伴被打倒后,士兵们都本能地伏低身体,顿时整个明军的阵地就矮了一截。战兵背后的辅兵本来就是壮壮声势,必要时帮忙背背伤兵,抓抓俘虏,虎蹲炮的轰鸣让他们感觉好像遇到了妖怪一样。没有人知道如何对付这种攻击,恐惧因而迅速在明军中蔓延开来。
“让火炮停一下吧?”
看到几炮过后明军就队形散乱,无论前排后排都惊慌地蹲下甚至趴下,被炮声震骇得已经失去抵抗意志了,绿营顿时跃跃欲试,打算冲上去把明军击溃。清军中没有进行步炮协同的训练,基本战术就是炮兵先轰,骑兵、步兵看着;然后披甲冲锋,炮兵看着。见汉八旗还在吆喝着给虎蹲炮装弹,绿营的军官就建议汉八旗中止射击。
“等会儿,我们还没杀够呢!”指挥炮组的八旗兵狞笑着说道。满清的中央部队已经很多年没有上一线了,就是偶尔出发也是作为监视部队随行。今天对面的明军毫无还手之力,这些炮兵可以肆无忌惮地轰击对手,这让每个八旗兵的脸上都满是兴奋之色。
打得兴起的满八旗完全无视绿营的要求,继续炮击着明军阵地,绿营军官指挥不了八旗部队,只能在边上看着,毕竟他们不想在带队冲锋的时候,背上中了友军的炮弹。看着几轮炮击就让明军抬不起头来,一线的绿营军官心中都十分羡慕,不少人都暗暗想着:“要是我们也能有各种大炮就好了。”
一直打到炮管开始发烫,八旗兵才意犹未尽地住手,八旗兵指着对面已经乱成一团的明军,得意地叫道:“打扫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确认八旗兵都差不多过瘾了,不会再开炮后,绿营也点燃了号炮,随着一声跑响,大批绿营披甲呐喊着冲了上去,对面的明军已经濒临溃散,任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占便宜、拿功劳的时候了。
其实虎蹲炮给明军造成的损失非常有限,这么长时间的乱轰一气后,被打死的明军只有十几个而已,但对士气的打击是无可挽回的。当绿营蜂拥冲上来的时候,后排的明军战兵二话不说,站起来拔腿就跑——那无法防御和反击的炮击总算中止了,他们可不想再挨上一轮。
前面的明军表现得也差不多,刚才的炮击让大部分明军士兵都心脏狂跳,颇有种在鬼门关前走了几个来回的感觉,这些被吓破胆的明军哪里还有斗志?绿营冲到明军的阵地上时,只有极少数特别勇敢的明军还试图抵抗,不过这零星的英勇行为毫无意义,转眼间他们就统统被淹没在绿营士兵的潮水中。
刚才听到炮声后,袁宗弟立刻派二百士兵回头去增援西线,希望能够让另一条战线坚持得久一点。可这些甲兵根本没能赶到前线,他们前方是大量逃过来的辅兵,其中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看到西面的同伴大呼小叫着逃过来,就也跟着一起跑。这些辅兵挡住了援兵的去路,而且他们还逢人就喊,称西面杀过来的清军铺天盖地,火炮打得和下雨一样,沾到就死、擦到就亡。在这些越传越广的谣言中,似乎整个西线的明军都被清军的火炮炸上了天,连他们用来坚守的丘陵都被削平了。
这些呼喊不但导致所有的辅兵都开始逃窜,袁宗弟派去增援的战兵的士气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官兵都没有信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那无坚不摧的火炮。尤其是有些人还听说过,邓名曾经用火药轰平了湖广城墙,自己的身体就算再结实,难道还能和城墙相比不成?和那些在一线的不同,援军中越是对火药威力有了解的人,越是高估他们没能亲眼看到的汉八旗火炮威力。
援兵本来就走得不快,随着士气一堕,他们就迅速地被涌过来的败兵冲散了,二百兵眨眼就被乱兵卷走了一半,剩下的也停止前进,不久后又开始缓缓后退。
“不就是虎蹲炮吗?至于被吓成这个样子吗?”袁宗弟看见原本被保护在两道防线之间的辅兵已经溃败,心中又急又气,他对这种武器的威力有直观的认识,惊惶的传令兵一本正经地把谣言报告给袁宗弟听的时候,他怒喝道:“听上去最多也就是十门炮,几千人就是让他们轰上一个月都轰不死!”
不过发脾气也没用,袁宗弟的见识对眼前的混乱毫无帮助,他不得不再次分兵,阻拦溃兵冲击自己的战线,命令战士们向溃兵呼喊,让他们自行逃向北方,等待收拢或是返回万县。忙着调整战线的袁宗弟自然再也无力向张勇进攻了,现在他只能祈祷张勇不要趁机杀出来夹击自己。
在袁宗弟的东面,张勇一直认真地观察着明军的动作,王明德的攻势比他想象得要快,本来张勇还以为需要联络一会儿才能见到援军主力出动。
“这小子,他是不是早就到了?”张勇嘀咕了一声,几乎狼烟一起,炮声就跟着传来,而这股狼烟也差不多是在袁宗弟发起攻击的时候点燃的,这行动未免也太紧凑了。不过只要此战取胜,张勇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王明德完全可以声称他是为了让袁宗弟发生误判,把主力从最重要的地段调离。
“王八羔子。”张勇哼了一声,虽然感觉王明德有点拿自己做诱饵的意思,但他也不是很生气,袁宗弟的攻势相当无力,根本没有给自己造成大威胁:“我先按兵不动,等王明德和袁宗弟的主力打起来,我再出击,这样损失小,还能多抓些俘虏。”
除了心里的整个如意算盘,张勇也明白在这个天气主动进攻会让士兵体力损耗很大,虽然身处树林中基本不动,但张勇也已经是满身大汗了。七月的川东又湿又热,披上全套盔甲后更像是拥上了一套棉被。袁宗弟的士兵已经打过一仗,现在又来回调动,张勇估计明军再这么奔波一会儿,他为取胜需要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这时来自北面的喧哗声打断了张勇的沉思,他侧耳听了片刻,心中大骂一声:“不好!”
骂完之后张勇急忙回身登上背后的丘陵,映入他眼中的就是铺天盖地而来的己方溃兵。张勇和袁宗弟一样把无甲兵保护在两道防线之间,现在张勇的无甲兵也已经全面崩溃,仓皇向着张勇的将旗方向涌来,以寻求统帅的保护。
沿江防守的另一半亲兵营且战且退,似乎遭到了很大的压力,比他们更糟糕的是张勇部署在北面掩护自己的部队。统兵的一个清军将领光着脑壳,连滚带爬地跑到张勇面前,哀嚎道:“提督!大帅!崩了,崩了啊!”
“混账!”张勇知道这个将领手下也有几百亲兵,没想到他居然这么一会儿都顶不住,袁宗弟还没崩溃,他就孤身一人地逃到了自己面前:“你连群新兵都打不过吗?”
“末将的兵也多是新兵啊。”那个将领刀鞘是空的,刚才为了逃命连武器都扔了,他极力为自己辩解:“贼人好多!好厉害!真的好厉害啊!”
“胡扯!”张勇根本不想听对方的胡言乱语,自己虽然顶住了袁宗弟的近卫,可这些无能之辈竟然麻痹大意,被一群乌合之众打垮了。
不等张勇戳穿对方的夸大之语,只见侧翼红旗闪动,大批明军从丘陵周围冒出来,他们身上的盔甲如同繁星一般的闪亮。张勇目瞪口呆地看了片刻,更多的明军士兵追着中路溃败清军的脚步出现在了张勇的将旗前,让空地和林间到处都闪烁着金属的光泽。
“成百上千的甲兵。”张勇喃喃地说道,他看到的正是中央突破,然后向南旋转的万县主力营。
“不要怕,不要紧!”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张勇立刻开始安抚有些骚动的部下:“王总兵的一万大军已经到了,马上就到!”
张勇先是向东面看了一眼,那里的亲兵正努力抵抗着明军的进攻,对面的甲兵是清军的两倍。虽然清军大部分是经验不足的新兵,但因为有亲兵营几十个老兵作为骨干,不但没有吃亏反倒能有秩序地撤退。面对清军的严整队形,沿着江岸进攻的明军也有些心虚,随着清军步步后退,明军大声吆喝着,清兵退一步明军就跟进一步。
张勇知道绝对不能让正在交战的亲兵营马上脱离战斗,现在靠着骨干老兵,四百亲兵还能克服恐惧服从命令,一旦在重压下仓皇后退,马上士气就会跌落到谷底,而且对面的明军也会声势大振,蜂拥而上痛打落水狗。
西面的袁宗第已经转入防守了,张勇就让逃过来的散兵去监视袁宗第,把精锐的一半亲兵拉过来防守将旗。张勇决心下得很快,趁着明军开始整顿阵型的时候,张勇的战术调整也飞快地进行着。虽然人数居于绝对劣势,但是张勇自问久经阵仗,应该能够坚持到王明德和袁佳文弼来增援自己。
在陕西提督的大旗对面,左佑挺直腰杆,紧紧地盯着那面绿旗,身后的部下正在排列成队,利用这个间隙左佑掏出腰间的水壶,稍稍地饮了一口水。
盔甲下的衣服已经被彻底浸透了,汗珠从头盔下不停地涌出,在脸颊上形成细流,汇聚到下巴尖上噼里啪啦地滴落。随着一口水入腹,大汗更好像一下子从全身的毛孔上同时喷出,厚实的盔甲下面,左佑感觉自己快要像炸药一样地爆炸了。
在万县对谭诣一战中,左佑就是邓名的贴身卫士之一,吴三、武三他们都和左佑是过命的交情。上次见面的时候,这几个家伙都改了名字,听说还是邓提督给起的呢。围攻重庆的时候,邓名还特意到袁宗第的营中,和左佑等几个并肩作战过的人把酒言欢,回忆万县的大捷——那是左佑最值得回忆的一仗。不过吴三他们可不止了,他们的战争经历要比左佑精彩得多。
虽然有一些羡慕,但左佑也没有丝毫的怨言,袁宗第是他的恩主,大昌的同伴还需要他。这三年来袁宗 第把左佑一直提拔到千总的位置上,带着主力营的一百多战兵,还帮他娶了亲。左佑对邓名是尊敬,但对袁宗第却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这是善待他、栽培他、需要他用性命去回报的恩主。
“全体——向右看齐。”左佑见部下基本到齐,就发出了口令。这些口令也都是邓名传授给万县军的,吴越望还亲自跑到左佑的队里,帮着他熟悉口令、训练士兵,而效果也非常好,让左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套口令。
“沿着我的手臂——旋转。”左佑伸平手臂,让全队的士兵调整好角度,其他的队官也都和左佑用着同样的口令调整着队形,很快主力营就朝着张勇的方向调整成一道整齐的战线。
眼前的敌将,左佑也曾听说过他的大名,张勇是袁宗第的老对手,而且据袁宗第所说,此人不但经验丰富,而且逃跑功夫更是一流。崇祯十四年到十六年,闯营在河南先后给秦军以三次歼灭性的打击,秦军在河南损失的军队前后高达二十万人,等孙传庭把甘肃、宁夏、陕西的三边军两次送给李自成歼灭后,秦军的基层军官为之一空,明王朝就此回天无数。世袭的秦军将门、军官、老兵十分之八都覆灭在河南战场,而张勇则是其中的异数,秦军屡屡覆灭,但张勇每次都能逃出生天。
袁宗第的旧部在湖广消耗殆尽后,张勇就成为了袁宗第再也不敢轻视的敌人,因为张勇经验丰富,而且手下还有一支南征北战而积蓄起来的精锐骨干;而袁宗第则因为变得物资匮乏,只能自保而无法锻炼部队,更不用说歼灭张勇的亲兵部队。
“如果没有你们,本公恐怕不是张勇的对手。”上次重庆之战后,袁宗第曾对左佑他们这些主力营的军官说过这样的话:“便是有你们,张勇也不可轻视。如果人数相当,你们对上张勇的亲兵营也是下风。不过听说他多年带出来的精锐都被提督歼灭了,这样就好,就像当年在河南,为什么我们越打越顺,秦军越打越弱,就是因为他们反复被我们歼灭。”
恩主口中的劲敌就在眼前,左佑和他的同僚们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决心用事实证明自己才是更强的一方:要是连这营张勇重建的亲兵都打不过,那不是太让恩主失望,也给邓提督丢脸了吗?
“前进!”鼓声响起,左佑大喝一声,带着部下们向前大步走去,他的左右两翼也同时迈开脚步。
“活捉张勇!”
“活捉张勇!”
不知道谁先喊了第一声,马上全营就一起有节奏地喊着这句话,其中也包括全体军官。
……
“弓箭手!”
张勇把一只手臂高高举起,已经有三百亲兵赶回来向他报道,有这些亲兵在身边,张勇顿时也是胆气一壮。他相信,很快东面的另一半亲兵也能退回他拒守的山头,一旦有近千亲兵严防死守,张勇根本不信袁军有实力啃下他的阵地。袁宗第的近卫的水平刚才张勇见识过了,如果不是形势不明,张勇甚至有反击打垮敌军的冲动——可是对面的这些明军装备非常好,让张勇看着有点眼馋。
看到对方整顿军阵的熟练程度后,张勇心里突然升起不安来:“难道这才是袁贼的近卫?”
刚看到这批人的装备好像比袁宗第身边的部队还好时,张勇就有些疑惑,不过他不认为袁宗第会和近卫脱离,所以觉得可能是另有原因,比如给近卫运输装备的辅兵迷路了导致装备落后,或者这是一批特意集中起来的敢死队,或是其他原因。
但对方的军容让张勇感到不妙,随着明军列阵完毕,张勇确定对方绝不是只有上百装备精良的甲兵,而是这一千多明军的装备个个都要超过袁宗第的“近卫”。
“放箭!”张勇用力地挥下手臂,清军的羽箭激射而出,洒落到明军头上,但明军的行动毫无停滞,依旧保持着原先的进攻速度。
“放箭!放箭!”
明军迅速地逼近,张勇连续不断地叫嚷起来,这时清军的弓箭手已经不用抛射,而是放平手臂,向着快速走上来的明军士兵进行直瞄射击。
弓箭不停地射中前排的明军士兵,如果弓箭没能刺穿头盔和甲胄,被击中的明军就行若无事地继续前进,甚至不会低头去看一看被击中的部位,或是去拔挂在盔甲上的羽箭。
“这都是上过战场的兵。”张勇已经得出了结论,不过他依旧感到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三年前袁宗弟打过一次重庆,输了,损失惨重;两年前他还打过湖广。就这两次吧,他怎么会有这么多老兵?”
有几个明军被弓箭重创,捂着喷血的伤口倒地,但他们身边的同伴依旧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还都是见过血的?”张勇知道新兵第一次见血,见到人死,尤其是同伴死在身边时,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新兵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往往刚看到敌人就口干舌燥了。刚才见到袁宗弟列阵而前的时候,张勇看得出有不少士兵两腿发软,手脚发颤,张勇暗笑这还是十日一操、吃饱喝足的亲兵哪。
“活捉张勇!”
明军最后喊了一遍这声口号,接着就换成了单字的喝声。
“杀!”
“杀!”
“杀!”
明军在走进清军阵地三十步后,一起发足疾奔,向着张勇发起全速冲锋,转眼间就和张勇的亲兵撞在了一起。
前排的张勇亲兵纹丝不动,持盾抵抗,抡刀反击,整条受到明军冲撞的战线上同时血花四溅,盾牌相撞的轰鸣声一瞬间就压住了鼓声。
刀光在空中飞舞,铺天盖地的杀声之中,张勇看到自己部署在后排的亲兵有人又开始瑟瑟发抖了,他亲眼看到一个初上阵的亲兵在敌人扑向他时,手臂软绵绵的连刀都举不起来了。那个士兵被对方一刀砍中脖颈,脑袋歪倒在肩膀上,摔向一旁;而那个看上去像是个带队军官的明军连喷了一脸的血都不擦,闪电般地挥刀向另外一个清兵砍去。
“还都是杀过人的?!”看着苦苦支撑的战线,张勇彻底呆住了,他脑袋里回荡着刚才那个丢盔卸甲的清军将领的哀嚎:“好厉害,真的好厉害!”
“袁宗第你会打仗么?把近卫放在后军?”转眼间,就有几十个亲兵被杀,明军虽然也倒下了一批,但一个个仍然势若猛虎,显然这营明军中杀过人、见过血的绝不只是个别的军官。
张勇终于发现,他和袁宗第一样误判了敌军的主攻方向,甚至他的错误可能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