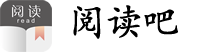永历十六年六月,万县。
“这都等了快一年了,成都答应给我们的粮草始终不到。”贺珍向刘体纯抱怨道。
根据川西和夔东的协议,进攻江南应该由川西独自完成,而夔东则负责压制重庆的清军。对重庆的压制工作并不算很难,有万县的水师就差不多足以完成了,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川西本身要出兵,所以答应给万县的物资并不是很多——足以保证水师作战,但陆军集结出动的物质并不充足。
“上次重庆之战还是去年八月呢。”贺珍对川西的安排称得上是异常不满,放着遍地黄金的江南不能去,却要去啃没有油水的重庆,贺珍感觉这近似一种羞辱。虽然川西答应补贴夔东,而且同意让夔东分享他们从江南的收获,但是从别人手里拿东西哪里有自己去搬好?只是贺珍的船不够多,力量不够强大,而且和东南各省的督抚也没有什么交情。听说川西部队在浙江的进展挺顺利,贺珍酸溜溜地说道:“看来以后我们只能从左都督手里分些剩饭剩菜了。”
又等了几日,上游有一批川西的船只经过,满载的船上有一些捎给夔东的货物。
“这是什么,象牙吗?这么多?”贺珍看到成都军官送来的礼物后,吃惊地叫起来。
“正是,这是保国公刚从云南运回来的。”成都军官笑着对委员会的诸侯们说道,整整两大捆象牙,都是邓名指定要立刻给委员会成员送去的礼物。
运货的船只上还装着好些中南半岛的货物,都是昂贵的宝石和象牙,一部分是明军缴获的,一部分是从托运士兵手中抽的税。还有一部分是参战士兵托运的财物,士兵们在交给军队时就同意让成都商行代他们出售。
在贺珍的强烈要求下,押送的军官不得不带着委员会的诸侯去货船上转了一圈。商行的伙计们也不愿意得罪这些将领,所以就允许他们在船上随便参观。有几个口快的伙计还告诉刘体纯他们,这只是第一批运回成都的战利品,据说后面的数不胜数。
“保国公的战事如何?”刘体纯问起缅甸的情况。
“听说已经议和了,这也是刚刚快马送到叙州的消息。”面前这位将领既是邓名的盟友,也是成都知府的父帅,川西军官自然不会隐瞒好消息:“这个消息是快马一路送来的,左都督大概还要几个月才能带兵返回。”
川西军官走后,委员会的诸侯们看着大捆的礼物,还是贺珍第一个开口:“当初去打缅甸的时候,左都督还说这一仗没有什么油水呢。”
这句话其实是冤枉邓名了,邓名从来没有和委员会这么说过,只是成都人普遍认为缅甸是蛮荒之地,大部分人根本没听说过富饶的丽江河谷的存在。而这个印象也通过成都人传到了万县,让贺珍他们有了类似的印象。
“左都督不让我们去打江南,也不带我们去缅甸。”贺珍抚摸着邓名送来的礼物,若是以前他能拿到这么好的几根象牙,一定会非常高兴,但现在却一脸的沮丧:“这么好的一根象牙,运到湖广换十根金子没问题。”
“还是因为我们是闯营呗,嘴上不说,心里总是不愿意我们壮大的。”党守素和邓名没有什么交情,这次不能去江南他也是心里非常地不痛快。
“胡说什么呢?”刘体纯呵斥了一声:“左都督和我们肝胆相照,你怎么能有这种糊涂念头?”
党守素重重地一拍桌子:“刚才你也看到了,船舱里满满的都是好东西,给我们的不过是零头而已。要是我们有这么一船宝物,能武装多少儿郎了?邓名分了一个夷陵给你,就把你美得不行,知不知道这是看大门的苦力?”
“胡扯!”刘体纯大怒:“你好不晓事!这次缅甸我们又没有跟着去,左都督人还没有回来,头一批战利品就想着要给我们送一点珍宝来,左都督这么惦念着,你却把好心反作驴肝肺!”
“你说的不就是我的话吗?不就是老贺刚才说的话么?邓名什么好地方都不带我们去,让我们去啃重庆,可是却不把粮草送过来,让我们就这么烂在万县。”党守素越说声音越高:“现在重庆空虚,明明很好打,可是川西不送粮食过来,显然是不想把重庆给我们!”
不管决定是参议院还是帝国议会做出的,夔东众将都认为这肯定是邓名的授意。即使刘晋戈、袁象和贺道宁来信说明,他们的长辈也是将信将疑,其他人更是认定了成都院会不过是在执行邓名的指示——对他们来说,如果没有自己点头,自己部下做出这么大的决定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上次万县的大败,李国英并没有向北京实话实说,他病好一些后,就竭力掩饰损失,帮忙一起说话的还有满汉八旗和张勇他们。重庆之战的惨败虽然没有全部 暴露,但还是引起了清廷官场的又一次震动,在谣言四起的时候,清廷不便努力挖掘真相,只能把重庆的失败大事化小。而由于西北的威胁,失去战机的赵良栋部队不能在重庆久留,看到明军没有进攻的意图后,就又返回西北——这一次大规模的调动算是徒劳无功了。
北京清廷还是不肯放弃重庆,听说十余万大军损失近半后,朝野已经是议论纷纷,这时再放弃重庆,就等于承认了明军的大捷和四川局面的彻底糜烂。
得知调来的甘陕绿营已经离开后,万县明军就一直想发动进攻,但成都方面表示粮食吃紧——既要供应东征、偿付建昌的垫付、更要保证储备,所以要等第一季的麦熟后才能提供,结果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邓名肯定是想等他回来,然后由他出兵打下重庆,好歹分给我们两个钱就算打发要饭的了。他就是信不过我们老闯营的人,他宁可带西营的人去,也不会让我们发财。”党守素气哼哼地扔下了这几句话,大踏步地走出帐篷。
留下的人面面相觑,刘体纯连着叹了几口气,只是不停地摇头。
片刻后,帐篷外又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党守素迈着大步又走回来了,进门后就让他的卫士去取那几根送给他的象牙:“我的东西忘拿了。”
卫兵抱着洁白的象牙离开后,党守素又扔下了一句话才走:“说好了开委员会,但第一个决议他就不执行,那这个委员会还有什么用?”
大家都感到十分没趣,默默地把象牙分了,然后各回各营。
刘体纯坐在自己的营帐里琢磨了一会儿,就起身直奔袁宗第的衙门,见到老战友后他开门见山地说道:“刚才党守素、贺珍的话,你怎么看?”
“党守素和邓提督不熟,贺珍更是个小心眼。”袁宗第安慰刘体纯道:“提督为人如何,你我心里还不清楚么?再说成都那边不是也说得很明白了嘛,现在根本是刘曜他们一伙人自作主张。”
“没有邓提督的授意?……算了,我不和你争这个。但人是会变的,老哥哥,将来三太子登基了,他会善待我们的,对吧?”
……
六月十日,袁宗第把刘体纯叫去,满脸笑容地把一封信递给他:“你儿子写来的,他说成都的院会已经把库存清点完毕,同意拨给我们粮草了,正在装船。”
“这倒是个好消息。”刘体纯仔细地看过书信,微微点头。
“小老虎也来了,据说一会儿就到,他的军队已经过了夔门。”袁宗第又告诉了刘体纯第二个消息,李来亨带着几千甲兵和大批辅兵来参与对重庆的进攻战。
“小老虎也来了?那荆州谁看门?”刘体纯吓了一跳。川西提出他们独自下江南后,委员会就达成了新的协议,汉水流域归郝摇旗负责,荆州一线由李来亨负责,万一张长庚发疯,明军也不会被湖广绿营打个措手不及。
“听说川军在浙江大捷,把浙江绿营和前去增援的福建绿营打得全军覆灭。现在张长庚肯定不敢翻脸了,留下一个郝摇旗就足够了。”
“什么时候来的消息?我怎么不知道。”
“刚收到的。”袁宗第解释道,当川军报捷的使者抵达荆门后,李来亨就整军出发,和捷报一起到达奉节,然后就快马通过云阳把消息送来万县。而李来亨带着贴身卫队也下船骑马而来,就在送信使者的背后。
“原来如此。”刘体纯说完后一愣,摇摇头:“这时间不对啊。”
按说报捷的使者抵达荆门后,李来亨就算立刻打定主意增援,也需要一些时间准备,怎么能够立刻出发?这只能说明李来亨早就安排好了一切,就等着这封捷报了;甚至没有这封捷报他本来都打算出发。
袁宗第沉默了片刻,刚才他也想过了这个问题:“反正小老虎这就到,你一会儿问他好了。”
一身披挂的李来亨看上去英气逼人,他走入袁宗第的衙门后,恭敬地向袁宗第和刘体纯行子侄礼:“袁伯父,刘叔父,来亨拜见。”
互相问候完毕,刘体纯重复了刚才向袁宗第提出的疑问。
“邓提督太小看我们的战斗力了。”李来亨直言不讳地说道。他确实早就做好了准备,听说成都迟迟不给万县提供军粮后,李来亨还自己筹备了一些,也已经运来了:“重庆现在只有李国英的万把战兵,而我们有两万多甲士,小侄这次又带来了五千人,有一个月应该就能拿下重庆了吧。”
“粮草的事情不必担忧。”袁宗第把刘晋戈的来信交给李来亨过目,告诉他成都会给万县运来运粮,不过成都的人手不够,需要万县自己筹备辅兵。
“如此就好。”李来亨接过信时表情显得有些复杂,而看完信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刘体纯察言观色,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一开始李来亨还支支吾吾地不肯说,但听刘体纯把党守素的话复述了一遍后,李来亨也轻叹一声:“我也觉得邓提督和我们老闯营的人似乎是有些疏远了,但看上去又不像,他一直重用我们的人,还用三堵墙当做卫队。”
“这次不就是用刘曜他们来分权了么?”刘体纯当着其他夔东将领不会说这种话,但在场的三个人都是和邓名关系最密切、感情最好的人,所以他也就不同担心会因为这番话而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刘曜、杨有才的底细我们还不知道么,根本没有治理政务的本事。”
“要说他们俩也不是完全不行。以前我们都觉得邓提督有点狼吞虎咽,怕他的内部不稳,可这次川西不但能一只手打缅甸,还能派出五万人下江南。”袁宗第对于成都的动员力感到非常惊讶,刘体纯、李来亨的领地人口加起来要比成都的人口多得多,如果再算上汉水流域的贺珍和郝摇旗,那更是川西不能比的,但他们几个人可无法同时进行两路远征。
“这应该是邓提督的手段,刘曜他们只是依照吩咐行事。”
不管儿子的信里怎么说,刘体纯对川西的体制还是完全不能理解。刘晋戈第一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第二刘晋戈也不明白这种体制的动员力到底从何而来,刘体纯从未到过川西,所以刘晋戈也就无法说服他父亲相信院会确实拥有这种能力,而不是邓名在幕后主持一切。
李来亨轻轻地点头。这次川西院会一点面子都不给夔东众将,让他也感到有些难受,和邓名以前给他的印象完全不同;不过出于对邓名的信任,李来亨也主动替他解释:“终究还是贺珍他们太不争气了。”
邓名威压湖广、两江,而郝摇旗他们连张长庚都打不过,就是李来亨和刘体纯,其实真要和武昌硬碰硬多半也不占上风。
“说得不错,应该和我们的闯营出身没有关系,三太子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至少在口头上,袁宗第始终站在邓名一边,不遗余力地否认邓名在提防夔东众将:“三太子亲口和我说过,闯营造反没错,你们看,成都现在可说过一句对闯营不利的话吗?”
……
七月,成都。
现在川西人一片欢腾。最新从云南传来的消息说,邓名已经回到国内,踏上了返回成都的归途;而下游也传来捷报,之前坚决主剿的浙闽总督集结了对抗明军的部 队,结果被川军打得丢盔卸甲。浙江沿海门户洞开,川军报告解救了大量的渔民和水手,已经达成了战略目的。下江南的部队收获很大,看来没有必要继续进攻山东了,估计现在也开始返回四川了。
相比重庆一战,这次明军下江南又是全国震动,湖广和两江都向北京报告,虽然他们誓死保卫了城池,但明军所过之处哀鸿遍野,府县残破,要求为大片的领土申请免税。而浙江的失利更是影响巨大,明军对下游的攻击已经频繁到了几乎一年一次,攻击范围也越来越广,而清廷对此束手无策。
虽然清廷不断声称明军遭受重创,就是高邮湖一战后,清廷都强撑着说明军也损失惨重,但“损失惨重”的明军又一次来江南,而且这次传说兵力居然有十万,显然清廷的说法非常可疑。要不是因为有君父之仇,说不定议和的呼声就会再次出现了。
“这次官兵又挣了不少钱吧?”成都书院的陈佐才把体育老师格日勒图叫来问话。
“禀祭酒,应该是挣了不少吧。”虽然格日勒图当上了议员,但那只是个头衔,他的日常工作依旧是在书院教体育,也靠这份薪水生活。
每天都有南征的战利品送到,就是说官兵没挣到钱也不会有人信。
“好吧,以前说过给我们书院马匹,这次也该给了吧?”陈佐才严肃地说道:“还有书院的经费,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些?”
“祭酒啊,这个可不是议会说了算,要是没有议院的许可,议会不会提案啊,就是提案了也通过不了。”正如刘曜理解的那样,现在议会基本是参议院的下属部 门。格日勒图知道陈佐才是想让他去议会要钱,连忙向陈校长解释:“我也就是挂个空名,什么时候参议院要有提案,我就去投个票,这要钱的事我办不到啊。”
“你总能见到参议院的人吧?”陈佐才吩咐道:“你去和他们说。”
“遵命。”这事格日勒图倒是能干,他以前的统领就在参议院里,晚上去汇报一声就成:“不过让我去说,还不如祭酒去说有用。”
“你就代表我了,我哪里有时间?”陈佐才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左都督对文人有很大的成见,他迷信武力。”
陈佐才前些日子抽查了一些亭里授课老师的工作,发现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字迹都不堪入目,而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老师很多都是速成的——先让招收来的读书人教徒弟,然后再由这些徒弟(包括女老师)去教新学生识字——邓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迅速识字,至于字体写得如何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
但陈佐才不同,他认定字体是至关重要的,开蒙的时候就要让学生把字写得工整,这样才能一辈子受益。于是陈佐才修改了邓名的教育体系,命令所有的读书人都要下去带学生,保证每个受教育的人都能得到充分的指点。
“一个老师只能带几个学生,怎么能够几十个人一个班?左都督当教书是练兵吗?”陈佐才越说越是气愤,他已经多次在公共场合声称这是邓名在有意地刁难读书人,给读书人穿小鞋。不过即使是几十个人一个班,陈佐才也坚持要求学生达到私塾的标准,自然老师们只有超负荷地工作。陈祭酒现在还兼着两个班的书法老师,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给学生上课,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这让陈佐才的心情更加不好,认定邓名是有意地为难读书人。
格日勒图领命而去,第二天兴冲冲拿着一张请柬跑来向陈佐才汇报:“参议院明日有个挂匾额的仪式,刘议长他们请您务必参加,还说会当面听取祭酒的要求。”
“可我明天有课啊。”陈佐才第一个反应就是推辞。
“只要祭酒去一趟,这件事不就解决了嘛。”格日勒图同样盼着赶紧解决马匹的问题,他已经不情不愿地与毛驴相处了太久的时间。他是马背上的勇士,不能整天教小孩如何骑毛驴啊——要是突然死了,都没脸去见地下的祖宗。
“好吧。”陈佐才斟酌一番,觉得确实不能再拖了,老师们都拼命加班,自然要付给更多的薪水来酬劳。陈佐才翻了翻自己的日程表,叫来一个仆人:“让明天那两堂课的学生今晚来,我先给他们上了课再说。”
如果邓名见到第二天陈佐才到达参议院时的风光,他就能明白为何自己一提办书院,就会让李定国他们胡思乱想。
议长刘曜和全体参议员都出来欢迎,好多人还口称:“老宗师来了。”
其实陈佐才并不算老,不过他的地位却差不多算是宗师了,因为他是书院的祭酒,所有的老师都可以说是他的弟子。现在成都各界都有去书院学习认字的人,都可以算是陈佐才的徒孙或是重徒孙。而既然是宗师,那一定是老的。
刘曜今天心情很好,今天牌匾上的那几个大字是他的手笔:一饭之恩不忘。
名义上是号召成都人民始终记得左都督的恩德,但其实也隐含着对刘知府的示威,告诉对方青城派是不会忘记昔日的仇怨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罢了。
一早就有很多来道贺的人,看到那块牌匾的时候,都会先问上一句:“这上头写的什么字?”然后就是赞美之词:“刘议长笔力过人,苍劲有力,很有武人风范啊。”
陈佐才到了之后,盯着那牌匾看了半天,问出了同样的问题:“刘议长你这写的是什么?”
昨晚为了给学生讲课,陈佐才的睡眠收到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眼睛里密布血丝,心情也更加焦躁。
刘曜满脸堆笑地亲自给老宗师讲解起来。
“一饭之恩不忘?”陈佐才嘴里念叨着,红着眼盯着匾额又看了两眼,突然叫道:“刘帅,你的书法是他教的吗?”说话的同时,陈佐才手臂向后一指,定在了跟着他一起来的格日勒图身上。
半晌,陈佐才背后传来一句委屈的声音:“祭酒这话也太伤人了,我会写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