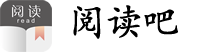第二面军旗展开了,看到上面三堵墙的图案,川陕督标顿时都目瞪口呆。
“难道这也是巧合?”老实人傅山叉不相信地问了一声。
和平主义者姚长尊根本顾不得回答他,转过头去声嘶力竭地冲部下们呼喊着:“谁有白布条,赶紧拿出来!”
这时邓名已经披挂齐整,骑着他的坐骑一溜小跑从阵后来到军前,所有的卫士都穿着黑衣黑甲,只有邓名仍是大红的军服和斗篷,身上的银甲也被映红了。
当邓名出现在战场上后,顿时吸引了全部人的目光,三堵墙和游骑兵都安静地等待着指挥官就位,而旁观的山东好汉们则发出了一阵阵欢呼声。那些被俘的绿营军官呆呆地望着邓名,从现在到世界末日,他们都不会忘记保国公的模样。
在忠诚的卫队之前勒住战马后,邓名看到熟悉的对手停在战场上原地不动,他知道自己现在肯定是在场所有人注目的焦点,刚刚对小姑娘自我吹嘘了一通,邓名暗暗给自己鼓劲:“是我露一手的时候了。”
看到那个红色的人影出现在对面后,傅山叉终于破口大骂起来,他确信不是碰巧有人长得和邓名一模一样:“熊森!我说他怎么把这么个美差给我们,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们哪!这个不仗义的孙子,居然不告诉我们邓提督来了。”
“要是告诉你了,你还会来么?”姚长尊哀怨地叹了一声,他正在忙着把白布条往枪杆上缠:“就是我们人多也打不赢,可是现在他们的兵马比我们还多。我可不想死在山东。”
“来不及了。”眼看对方就要冲锋了,傅山叉跳下马,转过身对兄弟们挥舞着双手:“下马,下马!我们要议和了!”
看到川陕绿营纷纷跳下马,邓名叹了口气,把刚刚抽出鞘的马刀垂向了地面。不出邓名所料,紧接着他就看到一条白布从对方的阵地里举了起来。和川军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川陕督标非常清楚川军的规矩,举起白布就表示要求和谈。
邓名轻轻一夹马腹,就向对面跑过来,而身后的一排卫士也紧紧地跟上。对面只过来了两个人,远远地邓名就看到他们满脸堆笑,不等双方靠近,他们两人就滚鞍落马,还把佩剑拔出来远远地扔在地上。
邓名凑近后,先是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才缓缓下马,背后的卫士们也整齐地下马,人人手扶剑柄站在邓名背后。
“你是傅山叉。”邓名再次发挥出美术生记忆容貌的特长,对面两个人都是川陕督标的队官,也都在他的战俘营里住过一个多月:“你是姚长尊。”
“正是卑职,邓提督好记性啊。”姚长尊走过来的时候,一直高举着手里的白布条拼命挥舞,唯恐邓名和黑衣骑士们视而不见。邓名刚见面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姚长尊真是受宠若惊。终于不用再摇晃了,把布条放下后,他急忙热情地与邓名打招呼:“邓提督,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你们来这里是想夺回驿站的吧?”邓名冷冷地问道:“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好了,我是不会还给你们的。”
“邓提督误会了,误会了!莱州知府是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另外有事,我们是路过的啊。”傅山叉连忙摆手:“我们是奉命去济南,这里有山东总督的手令,邓提督请看。”
两个人递上了祖泽溥的调令。在邓名看的时候,傅山叉还在边上解释:“莱州知府确实想让我们和邓提督打一下,可我们怎么会这么不识好歹呢?我们本想绕道从南边回济南,可是转念一想,和邓提督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了,就厚颜来借路。不知道邓提督能不能放我们过河去——如果邓提督不放,我们马上就走,绝不在您眼前添乱。”
“你们早就知道我在这儿?”邓名怀疑地问道。
“倒不是早知道。”傅山叉和姚长尊不敢撒太大的谎,就含糊其辞地说道:“刚才一看盔甲就知道了。有人想退兵,可是卑职决定留下来看看,如果邓提督在,我们就过来借路;如果邓提督不在,我们就从南面绕。”
邓名沉思了片刻,反问道:“我为什么要放你们过去?”
“那我们立刻就走。”傅山叉说着就要转身,但被姚长尊一把拉住了,他从邓名这句问话里察觉到了一种暗示。
“邓提督要怎么样才能放我们过去?卑职还不晓得。”姚长尊赔笑问道。
“我肯定不能放你们这样回去的,我不想让莱州官府知道我来了。”邓名坦率地说道:“如果你们要跑,我们就追击,箭射刀砍,总之是要全力把你们留下。”
“那我们就留下。”傅山叉立刻就表示他不走了:“虽然卑职身上没有优惠券,但只要邓提督今日放过卑职,那等回到重庆……”
姚长尊又拉了傅山叉一把:“听提督把话说完。”
“你们要写几封信,就说你们收复了驿站了,但马上要去济南了,或是找个其他什么借口,让莱州府赶快派军队来。”邓名也不和他们两个客气,立刻就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你们自己挑几个使者回去报信,把莱州府的兵马都引来……嗯,现在莱州府有多少兵马?”邓名扫了对面两个人一眼:“我需要把你们两个分开问么?”
“不需要!”傅山叉和姚长尊异口同声地保证道,他们赌咒发誓绝对不会有所隐瞒,一会儿邓名也可以向他们的手下或是其他的俘虏核实,若是有半句虚言,任凭邓名处置。
“好吧。”在听完两个人的汇报后,邓名就把他的条件摆出来:“你们先把马交给我,自己找个地方扎营休息去,不用解除武装,我保证你们的安全。等你们的使者把莱州的兵马引来,我就放你们过河回济南去。”
傅山叉和姚长尊都觉得这会给他们带来风险,将来若是邓名不能把莱州的官吏都灭了,他们说不定会被追查。
“不按照我说的做,今天你们就过不去了,也就不用琢磨以后了。”邓名见两个人哼哼唧唧的,眉毛就竖了起来。
“就按提督说的办。”姚长尊马上答应下来,他觉得只要认真筹划一下,还是有办法糊弄过去的。
邓名同意帮他们打掩护,而且也不管他们到底怎么糊弄莱州官府,只要把熊森的机动兵力骗来就可以:“等你们到了济南,就告诉祖泽溥确实是我来了,而且兵强马壮,大有席卷整个胶东的架势。不然,我就把你们和我议和的事说出去。”
“明白,明白。”傅山叉和姚长尊点头告退,他们回到自己的阵地商议了一会儿后,就又来向邓名报告,他们会派五个靠得住的兄弟回去通报莱州府,剩下的人都等在这里,直到完成了与邓名的协议后再一起离开。
“很好,要是你们能够顺利脱罪,回到重庆,我会根据你们引来的人数付钱给你们,当然要刨除你们的过路费。”邓名让督标里的军官都去明军的营地里休息,然后派人去监视剩下的士兵。
那些被拉来观战的俘虏看到这次来的是川陕督标后,心里还颇有些期盼,指望川陕督标大展神威,击溃这支突然出现的明军,把自己拯救出去。等他们看到川陕督标下马后,俘虏们就感觉不对了,但还没有搞明白这帮人到底在干什么。只见川陕督标的人举着白布条和保国公谈了一会儿后,所有的川陕督标都交出了坐骑,然后列队走向灰埠驿的后方。
“没事了,回去干活。”
随着邓名一声令下,押解俘虏的人就又把他们带回工地上去。这时俘虏们才恍然大悟,他们离开的时候,有人冲着傅山叉等人大叫:“你们甘陕绿营,打都不打就投降了!”
“你们懂什么。”傅山叉反唇相讥:“我们这是议和。”
愤懑不平的绿营俘虏都被带走了,更让他们愤怒的是,川陕督标得到的待遇还真和他们不一样,没有到工地上一起干活。
“邓提督,这些人不能留啊。”傅山叉对邓名说道:“要是让他们回去了,卑职们就有麻烦了。”
“你们知道我一般不杀俘。不过放心,只要你们办事牢靠,我会让闽军把这些人带去舟山,他们正需要人手修码头。”邓名保证道。
“多谢,多谢。”
川陕督标的军官和邓名在帐内说话的时候,吴月儿突然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指着这群清军军官叫道:“国公,把这些陕西佬交给我们吧。”
看到邓名的军营里突然出现了个女郎,说话还这么冲,清军军官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吴月儿是什么来头。
“这可不行。”邓名解释道,他已经和清军军官们达成了停战协议,只要对方履行约定的条款,那他就要执行协议。
“国公是担心名声受损么?”吴月儿飞快地说道:“这还不好办,把他们一个不留都杀了,不就没人知道国公毁约了吗?”
“这小娘好狠!”帐内的清军军官心里都腾起了这个念头,不过看邓名和颜悦色的样子,没有一个军官敢把这话说出口。毕竟邓名说话算数只是他个人的决定,并没有受到任何约束。
“因为这是协议,协议达成了就要执行。”在这个问题上邓名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他对吴月儿说道:“因为我已经答应了他们,所以他们的性命现在已经处于我的保护之下了。”
曾经听过的一幅画的背景介绍,让邓名很钦佩一个库尔德人,当时人都知道只要萨拉哈丁给的水,那他就算是安全了,哪怕是俘虏也一样,因为守信的萨拉哈丁会全力保护他的客人的安全。后来好像还有本小说借鉴了这个故事,把水改成了面包和盐,邓名刚才给了川陕督标的军官茶水,于是他就指着那些茶杯说道:“我已经请他们喝过茶了,他们都是我的客人,我不能让喝过我茶水的客人在我的营帐内受到伤害。”
虽然是盗版,不过邓名还是很满足,因为正人君子罕见得像是沙漠里的水珠,所以才令人向往崇拜;而看起来这句话对川陕督标也很管用,他们听清了邓名的发言后立刻都抓紧了手里的茶杯以表示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客人。刚才傅山叉觉得茶水太烫,他又不是很渴所以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浅尝上几口,听到邓名的话后,傅山叉举起还腾着热气的茶杯,二话不说就统统倒进了自己的喉咙里,一口全咽了下去。
“可我们那么多义士都死在了他们手里。”对邓名的坚持,吴月儿有些不能理解。
“这位吴先生——”刚痛饮了茶水的傅山叉正捂着喉咙说不出话来,这批川陕督标的另外一个领队姚长尊急忙挺身而出为大伙儿分辨:“邓提督在四川的时候就教导我们,战场无私怨,生命相搏的时候生死各凭天命,只要能活着进了战俘营,那就不会因为战场上是不是杀过人被追究;邓提督还教导我们,武人最不可饶恕的行为就是欺凌弱小,所以对百姓烧杀抢掠的休想得到宽恕。”
姚长尊左一句邓提督教诲,右一句邓提督训示,把吴月儿都唬住了:“吴先生一定知道,我们拿的是鞑子给的军饷,江湖上有句话说的好,叫做收人钱财,与人消灾,你们山东的好汉拿了雇主的银子,难道不去灭了雇主仇家的满门么?我久仰山东好汉的大名,想必不会做出这么不讲义气的事来吧?”
吴月儿一时竟是无言以对,而姚长尊得理不饶人:“而我们和山东好汉打仗,就是为了对得起我们拿着的军饷,而战场之外我们从来不祸害百姓,不杀害已经投降了的俘虏,则是出于提督的教诲,也是因为我们对山东豪杰们的敬仰——虽然我们拿了鞑子的银子,不得不和诸位好汉在战场上决一死战。敢问吴先生,我们有祸害过百姓,有杀过投降的义军俘虏吗?”
邓名冲姚长尊微笑了一下:“姚队正的口才是越来越了得了。”
“全是提督栽培。”姚长尊的回答倒也不全是恭维,和邓名做了几年邻居后,本来性格直爽粗豪的甘陕绿营,一个个讲起歪理来都越来越纯熟了。
吴月儿没能达成高云轩、邢至圣交给她的任务,离开邓名的营帐后,她垂头丧气地告诉两位师兄任务失败了:“你们比我会说,你们去和国公说吧。”
高云轩和邢至圣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吴师妹说都不管用,那就没有办法了。”
刚才就是他们几个撺掇吴月儿去找邓名要人,连名声什么的说辞都是高云轩的主意,见吴月儿脸上还有些不解之色,邢至圣还添了一句:“第一次见面国公就同意师妹上桌吃饭,显然……嗯……话说高师兄啊,这几个陕西佬说的也有道理啊,好汉们拿了银子也不能不去灭仇家而是反过来把雇主灭了门啊,那太没有江湖道义了。”
“算了,此事不必再想了。”高云轩悻悻地说道,他转身对吴月儿说道:“我和邢师弟现在都正好都没事,吴师妹和我们一起聊聊接下来的策略吧。”
吴月儿先是吃惊,然后就高兴地叫道:“好!”
虽然受到师兄的保护,但江湖上的事从来不会让她这个姑娘插嘴,更不用说涉及到战略问题。以前若是因为好奇要求旁听,父亲、和颜悦色的师伯、还会板起脸来斥责她不懂事,出门以来师兄也从来不会和一个姑娘讨论未来的大计,没想到今天高云轩和邢至圣居然提出来。
“高大侠。”
保国公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邓名知道山东侠客们对川陕督标仇深似海,刚才他为了贯彻自己始终如一的政策而驳回了吴月儿的要求,但这也给邓名敲响了警钟,让他意识到同样需要安抚山东盟军。
邓名阐述他的理由时,高云轩、邢至圣都一言不发地认真听着,等邓名告一段落后,他们两人一起点头:“国公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放心吧,以后不会再给国公找麻烦。”
说完后高云轩就扯了一把邢至圣:“国公恕罪,营里还有点急事,我和邢师弟还要赶紧去处理。”接着一指吴月儿:“就让吴师妹和国公说说我们山东军的情况吧。”
见吴月儿似乎要说话,高云轩抢在她出声前解释道:“突然想起来的事,很急!”
虽然堵住了驿道,不过暂时邓名还没有攻打县城的能力,他并不打算用自己的精锐卫队去巷战,而现在山东盟军虽然人数上千,但毫无战斗力,邓名正忙着帮高云轩等人竖立威信,帮助他们把来自几十个山寨的起义军组织起来。除了山贼以外,还有一部分原本是城市的少侠,义军被击溃后逃散到附近的山寨,虽然也是从山寨出来的但和山中的好汉也不是一个派系,让邓名的盟军成份变得更复杂。
“等到我把莱州府的机动兵力都消灭了,尤其是绿营的马兵,莱州府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和之前好汉们的山寨一样。”邓名给吴月儿讲解了他的战略,本来他是打算对高云轩等人好好讲讲的,以便让他们明白川陕督标的用处,不过高云轩等人有急事走了——邓名怀疑或许是对自己有怨气,不管是哪一种,都只要通过吴月儿转告了:“那时驿站上只会有我们的使者,很快全莱州府的义军就能齐心合力,到时候别说是县城,就是府城都很容易就能打下来。”
虽然邓名没有把川陕督标的人交出来,不过吴月儿对邓名的钦佩还是上升到个更高的高度,刚才见到邓名全身披挂站在军前时,虽然威风凛凛但还是忍不住担心这么明显的目标不要有什么闪失。但在山东起义军面前如老虎一样凶残的川陕督标,在邓名眼前却是乖得如同小猫,根本不用打就举着白墩布过来投降了——虽然傅山叉和姚长尊坚称是议和,但吴月儿认为这就是投降。
“国公果然英雄了得,那甘陕的鹰爪牙在国公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了。”
邓名闻言又是一笑:“吴女侠听说过‘鹰派’和‘鸽派’这两个词吗?”
简单解释了一下这两个词的意思后,邓名继续说道:“绝大多数的人,也包括我,都不会是单纯的鹰派或是鸽派,而是遇见老鹰就是鸽派,遇见鸽子就是鹰派,简而言之就是欺软怕硬。所以我们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只老鹰,那样我们遇到的就都是鸽子,而如果我们是一只鸽子的话,那满眼看过去都是老鹰——就像我信守自己的诺言,厚待议和的川陕督标,也是因为我没法做一只彻底的老鹰,因为我还没有那样的实力,可以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
邓名让吴月儿转告高云轩等人,他还是认为现在在山东开辟根据地为时过早,因此于七集团需要更灵活的策略。等山东好汉在四川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拿到了更多、更好的装备后,才是更合适的正面武装斗争时机:“不要看我扫荡驿站很轻松,战争的关键还是要有一支强军,要能堂堂正正地击败对手,化妆劫营什么的都是锦上添花罢了。”
很快川陕督标就完成了和邓名的协议,急急忙忙赶来莱州参将带着两千军队一头撞进了邓名的伏击圈,被山东盟军打了个全军覆灭——此战并非邓名独自完成,他只负责攻击清军行军纵队的指挥中枢,而大部分伏击和抓俘虏都是山东友军负责的。
把莱州的机动兵力全数消灭后,邓名如约释放了川陕督标,让他们回济南向祖泽溥告急,而邓名也愿意配合他们一下,交给他们一些旗帜,还让他们割走了被击毙的绿营士兵的首级,称他们是化妆成清军的川军。
川陕督标会告诉祖泽溥他们是拼死冲出一条血路突围的,而邓名确实在山东登陆了,正在训练莱州府的起义军,大有让整个胶东半岛重新陷入糜烂的架势。
不过邓名最后改变了注意,没有让川陕督标大肆夸大他的力量,而是告诉祖泽溥川军人数有限,靠的也是化妆偷袭,正面战斗力相当一般,所以川陕督标轻松地溃围而出,不但没有上伤亡还砍了几十个首级。
而在了解到了莱州的危局后,祖泽溥大惊之余,就很快下定了决心,一面上奏朝廷,一面命令集结在济南山东督标和提标倾巢出动,全力东进。